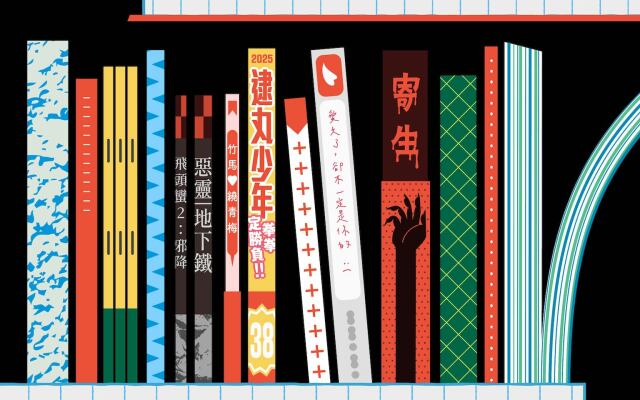【特稿】絕望之後的新生之書──夏夏《狗說》新書分享會側記
詩人夏夏繼第一本小說作品《煮海》之後,帶來了第二本小說《狗說》,如同夏夏詩裡的純粹,同樣是澄澈而純淨的結晶。不同於《煮海》中島與海的與世隔絕,《狗說》一書以都市作為背景,細細描摹養了狗與媽媽的日常,只是在熟悉的都市生活裡,卻依舊具有一絲寂寞、疏離的味道。
在遠流別境的新書分享會裡,透過郝譽翔的提問,與夏夏一齊帶領讀者進入《狗說》裡既魔幻、卻又倍感真實的世界裡。

關於夏夏的寫作,郝譽翔認為詩人的寫作需具有赤子之心、小說家則需較為世故,才能寫作,因此寫詩也寫小說的夏夏實屬難得。「夏夏的小說裡,有詩的特色,精粹、乾淨,同時帶有都會特質以及詩意。」在《狗說》裡沒有太複雜的文字,透過簡練、乾淨的陳述,所呈現出來的世界彷彿是刷白的場景,如果說《煮海》所呈現出的是海水蒸煮過後結晶的白色鹽粒,《狗說》帶來的則是都市裡飄忽的粉塵降落在桌上的安靜。
談及《狗說》的創作動機,夏夏坦言「是因為我的狗(小狐狸)死掉了」,小狐狸是一隻陪伴夏夏許久的柴犬,相遇時的故事十分不可思議,當時正讀著《小王子》的她,讀到了小狐狸那一章節,出門時便見到一隻柴犬伴在她的摩托車旁,夏夏喚道「小狐狸」,小狐狸便這樣跳上了她的車。途中小狐狸原先的主人曾出現過,將牠帶回去,但過沒多久便又希望夏夏收養牠,因為離開夏夏的小狐狸不願意吃任何東西、生病了,但就在回到夏夏身邊時一切恢復如往昔,至此,小狐狸便伴她,直到小狐狸死去。「狗是我的家人,我每天一回到家,就會對著牠講話。」離開原生的高雄,到達台北生活,夏夏形容小狐狸便是家人一般的存在,在小狐狸過世後兩年,她開始動筆寫《狗說》,直到《狗說》的完成,她才覺得與小狐狸真正地告別了。

作為一本紀念死去的狗的作品,談起死亡的書寫,郝譽翔認為透過書寫逝者,其實也是在釐清自己的感受,並且是一最好的紀念方式,其中有些情感會進一步地昇華。「這是一本不會讓你絕望的書。」她補充道。在創作《狗說》的期間,夏夏提及,在書寫中段時曾有一段長達半年的停頓,那時她甚至覺得「這輩子都不要再寫作了」在這半年的時間裡,她前去尋找失去小狐狸後生命的重心,最後她找到了、生命有了轉變,也讓原本前半段讀來十分悲傷、黑暗的《狗說》起了轉折,長出溫暖的力量。
在書中,都市與森林的場景交錯,書中的主角「媽媽」其實發想自夏夏對於母親的虧欠,「家庭的影響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深。」談起在台北遠離家庭的生活,長久以來對於母親理所當然的存在,因此讓夏夏對於母親這樣的角色有了許多疑問以及想像,在作品中將自己化身為媽媽,試圖描繪出母親的形象。在《狗說》裡,與媽媽外遇的對象名為「青光眼」,談起這樣的角色設定,夏夏表示:「在這本書裡,每一個人都是生病的人。」無論是與媽媽同住一個屋簷底下的爸爸、還是兒子和女兒,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著各自的病,在都市裡持續地疏離著彼此,也許就是在陳述著都市裡的每一個人所具有的孤獨與疏離。
除了對都市的描寫入扣,森林在夏夏筆下是另一主軸,「如契訶夫所言,『從自然中得到力量』。」談起生活在都市裡的自己與自然的斷裂,夏夏回想,反而是在養小狐狸的那段時間,帶著牠到附近公園散步,跟著牠一起接近泥土以及青草,「動物反而成了人類與自然的連結。」

在講座後,BIOS 向夏夏進行專訪,聊起對於《狗說》具有啟發的作品,先前記錄福島核災後《被遺忘的動物們》中所存在的流浪狗,令夏夏感覺深刻,談起開始養狗後,會開始關注與狗相關的議題,書中被遺忘的動物們依舊在原地等著主人,「動物對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夏夏這樣說。對於日前在台灣社會發生的動物權、狂犬病議題,夏夏謙道自己其實尚未具有將議題帶入書寫的能力,但期許自己未來能夠具有這樣的力量。





![[閒聊] 大家有在便利商店買過小說嗎? - 看板 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storage/upload/article/tw_article_coverphoto_20250515123328_qj2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