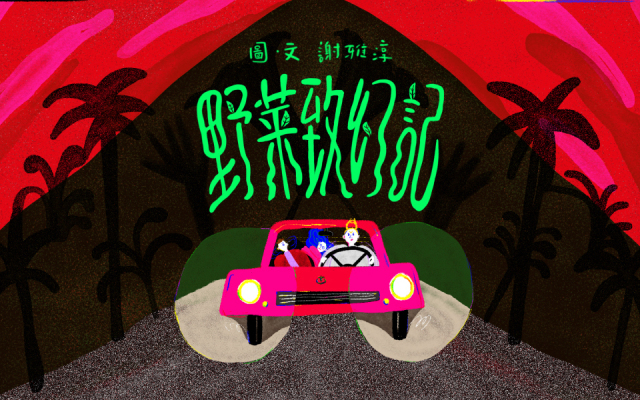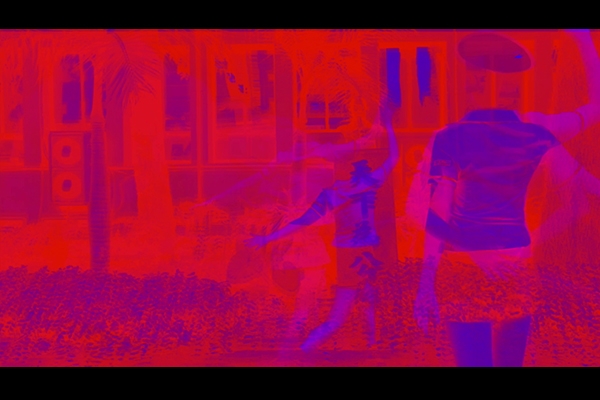
髒字帝國——談「超脫國歌」
〈超脫國歌 cha twat gringo〉這個音樂行動活動,藝術家鄭宜蘋,試圖將計程車做為一種展覽空間。在整個行為藝術活動的部分,鄭宜蘋在計程車前座,操縱後面影像螢幕,擔任解說員。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是置於計程車後座一件由女性角色不斷脫下內褲的錄像作品。在錄像作品當中,可分為三大部分,可分為一、重新定義其英文髒話翻譯;二、以國歌為主體,以英文髒話發音重新重唱國歌;三是倒帶國歌的部分。這個藝術家所宣稱聲音、行為、錄像、實境、表演,互相交織的實驗下,一方面在具歷史意涵的二二八公園與自由廣場的往返路線上進行。
車內首要的影像文本,如藝術家所言這個行動計畫是使用民國三十二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頒布的國歌為一文本,將歌詞內容重新使用英文黑話串聯為一新聲音文本。不過在語言的對譯狀態下,我們如何理解語言的理解狀態,以及語言藝術而非單純聲音藝術,在語言系統中的碰撞呢?以及對比鄭宜蘋在這個計程車車遊外在二二八與自由廣場所記錄的制服行動,是否達到翻轉如紀傑克描述官僚制度中暴力制服淫虐的快感,或是對比藝術家鄭宜蘋裝扮所呈現出的色情邏輯,這些色情符號系統的不潔還有足夠力道衝撞舊有體制?

從語言層面來看,漢語系統之中,語音近代理解的轉折可說是起於陳第。陳第認為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的區隔,漢字語音應該有所區隔。這觀點在顧炎武的《音學五書》中就曾利用著過去切韻的方式將語言細微的變化區分開來。而所謂切韻的方式是將利用兩個漢字前一個字的輔音結合後面字的韻母,加上平、上、去、入的音調進行分類。而漢字的理解,可說是一方面是來自佛教傳入帶來一種外部理解語言內部的過程,而顧炎武那種視語言不斷變化的過程,到最後在中國清代郝懿行將雙音詞視為兩個可以分離的單音詞。之所以要提及這點背景,而是語言認識下讓漢語文字符碼中,語音的理解一直是一種外部的入口,同時又由於雙音詞是為兩個可以分離的單音詞,使得雙音的詞常常受到切割產生意義的變化。
之所以談到漢語自身理解的轉向,是為了理解鄭宜蘋對於這些語言操作下的歷史痕跡以及言語技術。就是漢語過去藉由外部的理解再加上對西方的焦慮,漢語本身向外敞開的破綻讓每個人敞開,國歌的莊嚴表像,也有著色情想像的進口或出口。作為一名參與者,其實如果思考到所謂語言移轉(language transfer、linguistic interference)也就是鄭宜蘋使用語言學中的借詞,「音譯詞」與「意譯詞」的兩個層次上,或許對於藝術家也意外地沒有察覺可能無形達到除了批判臺灣國歌不適宜的政治狀態外,也包括了對美語本身的批判。在借詞中,有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是指一種語言,故意從一些地位比較低或者他們看不起的語言借用詞語,來指一些貶義的概念。這所謂的貶義借詞(derogatory borrowing),通常在臺灣內部的語言對比國語是台語,但這裡一次翻轉為在臺灣高呼國際化的美語髒話,反倒被貶抑了。用著這些髒話,也恰好得益於臺灣人在言語母體對於美語字尾的遲鈍,讓美語的對譯可以滲透於受眾之間。

當錄像中的女子掀開裙擺,車內的觀眾看著一件又一件的底褲,超- Cha -你、脫- twat -陰部,這些 R&B 常出現的黑話髒字,跟著國歌- gringo -外國佬,組成了語音鬆動下的批判。是否國歌與外國佬的指控到最後輸到脫完褲子只剩下黏著鈔票的畫面,是對臺灣國民黨與美國政權強烈指控?但如果如果回到這些符號,我們跟著進行一連串旁讀(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國民黨 - 美國的指控在藝術家鄭宜蘋這一次「超脫國歌」的活動,言語勝過音樂,事實上打開聲音形式中的語言意義。當所有觀眾如旅客穿訪原本熟悉的公園路、羅斯福路、景福門或是凱達格蘭大道,被鄭宜蘋的解說受限在計程車,有時又忽快忽慢地,最後又可能被安排在上車完全不同的地點下車。當計程車試圖打斷二二八公園與自由廣場兩個空間結點,或許就跟「超脫國歌」試圖重新打斷語言莊嚴意義的錄像作品,讓人期待這個髒字帝國日後還可以在聲音藝術的程度超越到哪個層次了。
展覽時間:2014.06.04
展覽地點:二二八紀念公園與自由廣場間遊走的計程車
【專欄簡介】
藝術作品不會主動地揭開它的深刻,本專欄將提供台灣當代戲劇、視覺藝術展演的介紹與論述。由「關係藝術」的理論,這勢必帶著藝術作品與文學之間的認知差距,但也希望藉由這些差距,討論作品的文化脈絡及其美學觀點,提供讀者進一步的討論空間。
【印卡】
七年級詩人,秘密讀者編委,詩歌作品散見於《自由時報》、《字花》、《衛生紙》、《創世紀》等刊物,曾被收錄於合集《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著有詩集《Rorschach Inkb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