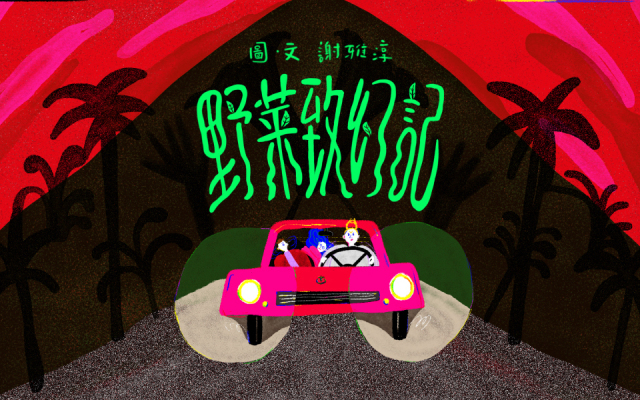我是吳十艾
我的名字是高克明。
『在黑暗中,時常飢餓難行,只能隨夢。今夜我領悟,也許我渴望虛無造字,留下比生理排泄更恆長的紀錄。』
※※※
我的名字是吳十艾。
這是一個怪異又帶有點異國情調的名字,每個人看到時都會愣一下,筆畫又不多,寫得快時筆跡草率更難辨認。我已習慣初次呼喊我的名字的人,總會微微皺眉,音調拉高唸到:「吳...十艾?」接著下一步就是掩飾微微驚訝:因為我是一個長相平凡到不行的男生。
不知道我母親當初是從哪裡得到的靈感,十艾,究竟有什麼涵義?我母親並不是一個喜歡與眾不同的人,更非追求新奇,又,十艾也不是一個怪到非比尋常的名字,卻也因為這樣而更難以辨認,面目模糊。
「十艾,我們分手吧。」這是我前前女友和我分手時的台詞,她的名字叫李冠寧。聽起來宛如喜劇般戲謔,真實發生在我們身上時卻笑不出來,她厭倦了再被叫錯名字或訕笑「應該和男友交換名字吧」,同樣地,冠寧也不是什麼非比尋常的名字。
冠寧是我的前前女友,而我的前女友則是一句話也不說就離開,無情地結束了這段關係。她從未抱怨過我的名字,但似乎,我在她心中是個頗為惡劣、不甚體貼的男人。
分手前夕,她正在一個出版社實習,每天工作繁忙焦頭爛額,面對我這個死研究生每日清閒讀書聊國家是非相當不悅,約會時若有不滿都寫在臉上,也不加以掩藏。從前,我喜歡她坦白誠實,今日想來,難免有點無奈心酸。
這麼說來,又是一樁諷刺之事:最後某次約會,我倆約在她公司附近熟稔的咖啡廳見面,我已窩讀一下午,美式黑咖啡已浸滿整個腦子,正是熱切懸浮於自己世界的時刻。她下班來到,點了冰拿鐵,就坐著發呆。「餓了嗎?」「還好。再坐一下吧,沒關係。」
她發呆看手機半天,也未打擾我的讀書進度。過了一會,才終於夢遊般地突然說道,今天去訪問了一名年輕的男小說家。那是一位我不算欣賞的小說家,我有些驚奇,她已有些時日不和我分享工作瑣事了,自從我總是忍不住碎嘴批評後,她已明白沒有什麼好告知我這個頑固而愛好發表意見的男人。「還順利嗎?」我疑惑地問道。
她沒回答我的問題,只是開始敘述小說家今日的言行。小說家年輕力壯,剛寫完一本融合史實和虛構的中長篇小說,這雖然只是他的第三本書,然而他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正是創作的大好時期。這樣和女編輯一對一的訪問,想必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時刻。果然,小說家有的問題雖拒答,有的則加以發揮。
說了半天,她才幽幽地補了一句:「其實,小說家有個頗女性化的本名。」「喔,真的啊,他也是嗎?哈哈。」
此話當時在我心中並未激起漣漪。
原來,他那印在書皮上,有點酷、卻又還算低調的名字,是他的筆名,那是個令人第一個念頭不會想到是個虛構的名字。這樣啟用一個虛構的名字、虛構的姓氏,使用虛構的血緣關係、躲在虛構的家族樹底下,是什麼樣的感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啊,我想他會這樣回答。虛構了一整本小說的他,大概不會說形同犯罪般不安吧。
那天半夜,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我可以幫自己取一個名字。那天起,彷彿從這個我厭惡的小說家那裡得到了某種天啟,我開始日夜思考著造名。我終於承認之所以對這小說家感到反感,應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喜好批評、擅長捕風捉影,真實心意總是不肯透露。
在那之前,我偶爾寫點日記書劄,是個學究派,必未對寫作本身有什麼興趣。在那之後三個星期,她一字未留再也找不到人。手機換了,家裡電話拒絕接聽,上班地方我也去了,在那徘徊一下午後,覺得也沒有什麼意義,既然她絕情至此,就這樣結束吧。我寫下睽違已久的日記,並不感到特別自責或愧疚,甚至想著,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離開她公司的馬路口,這麼多個月以來,我終於看見此段關係的終點。與她交往兩年五個月多,她算是真正了解我的第一人。也許也因為如此,她明白我並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之處。「總是看不見別人、也不關心別人的事情」她或許有這麼說過我?或許沒有?
馬路口清冷,垃圾很多。有兩隻狗打轉著彼此看不順眼,惡意盤旋。初秋的傍晚,蕭索可笑,初次感到事事皆茫然未果。
然而,原以為只是繼續孤獨,但是那天起,我心的惡獸開始龐大橫行。
※※※
在課堂上,我思考著讀研究所的意義,同學老師逐漸黑白失真,我的思緒飄向校園遠處。前女友的臉龐偶爾仍在人群中浮現,即使我總覺得對她沒有特別懷念,偶爾下半身激起對她體溫的需求,總讓我惶恐彷彿不像個真正存在的人。
我開始心生對那小說家報復的舉動。也許,是那小說家煽動了她,勸她離開我。到書局,我花錢買下了小說家的第一本處女作,一字不漏地看完。出乎意料的,我竟然有些喜歡,比起他後來冗言贅字的長篇小說,這本簡潔純樸的短篇小說集,更深得我心。其中許多個短篇,如《再會》、《台北地下世界》、《新的詩集》都寫得渾然天成。在《台北地下世界》中,小說主角愛上了一名在地下街餐廳上班的女人,然後有一天,他目睹她被流浪漢攻擊出手救援,因此兩人開始相戀。但不久後,他就發現女人曾和流浪漢有一段情,原來流浪漢因為她的背叛而發瘋,才失去心智。男主角知道這個真相之後,只是默默地搭乘電扶梯離開地下街,來到光明的地上世界。
「台北的地下街總是有種迂腐的氣息,皮鞋店、舊服飾店、書店和動漫雜貨,像是一座死城。他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愛上那個女人,除非,他本來就死去多日。看不見真實的靈魂橫陳。」
什麼是「看不見真實的靈魂橫陳」?我不明白,可我卻喜歡上這篇小說,僵硬生冷的文字,戲劇化的劇情有點令人反感,卻令我想到七等生等早期存在主義小說。
這本小說集命名為《暗室》,同名《暗室》的小說篇幅最短,放在書末,是一名讀書人的自我對話,有點類似書劄,似乎在哪個日本小說家的作品也看過類似的形式。讀完他的小說,我與這名小說家竟然好像靠近了一點,我想像著那天訪問時,她停留在他臉上的目光。
回家後,彷彿做夢醒來,我翻開筆記本,在空白處寫下「高克明」三個字。
我不算真的討厭「吳十艾」,它有一種莫名的曖昧性,口天吳,十,草字艾。「高克明」似乎有點普通,低調中帶有點哲理,也有一點可笑。
不過,其中「克」字即包含了「吳十艾」;有口,也有十和變形的乂。我似乎是一開始就這麼想的?想要取一個名字將吳十艾巧妙地包容進去,解消瓦解。可是,若沒有人先知道我是吳十艾,那麼高克明又有什麼奧義?
我不知道,本來就沒有意義。
讀完《暗室》後,我對他其他的作品還是提不起興趣。但仍忍不住上網查詢了他的 Facebook,果然他的動態時常更新,新聞分享轉貼時事書評,熱絡地與讀者互動,偶爾寫點心情,但大部分都沒透露自己的生活細節。看到他這周六晚上將於書店舉辦新書座談,就這樣,我如幽靈一般去了。
看到他本人時,我大吃一驚。
他本人舉止強硬冷悍,卻又透露出難以形容的幽微女性特質。長相清秀皮膚白,應是家世良好,從小備受寵愛。自負溫文,恐怕是在相同的世界裡團團轉著,追求突破。
突然間,我再次看到我自己,因而心生恐懼。默默聽完講座,我望著講台上的小說家,瞳孔中似乎流露憂鬱的神情:「你怎麼不了解我?」我甚至快發出聲音,幾近分裂地將他看成自己的一部分。
回家後,我終於開始我的第一次寫作。
於是我的第一篇小說,竟然就是個死阿宅被甩後的復仇想像罷了?
半夜的房間裡,聽著沉緩的音樂,冷冽的鼓聲如死亡之步伐。
※※※
在沒有她的音訊好幾個月後,我終於慢慢放棄追逐她和那名小說家。小說家的新小說風評不一,頗為極端,欣賞者稱他為華文小說的新浪潮,大膽而有說故事的能力;不看好者認為他言之無物,新書中充滿太多耽溺與不必要的敘述篇幅。
一日,我終於在街頭看到她。她穿著黑色風衣,像以往一樣忙著趕路,長髮紮起的馬尾垂下幾縷髮絲,帶有綴飾的耳環吐露出成熟的氣息。但是不論如何,那已經不是曾和我散步走路、吃同一碗麵、做愛並睡著的她了。
我忽然想起某個周末,我因為前日熬夜念書昏睡至中午,睡醒時她已不在身旁。我勉強從床上坐起,看見她背對著走道上窗戶的光,逆光將她的身形鋸成深黑剪影,垂著一頭黑髮,不知道在看著什麼。我赫然好奇她是否在看我閒置在地上的某本書、某本厚重的論文集,雖然可能性不高。她穿著透出身材輪廓的薄睡衣,雖然款式休閒,仍露出修長腿部。她似乎動也不動,如在夢中。
此刻我突然對她感到萬分的陌生,半蜷曲在地上的她,彷彿一隻惡黑的烏鴉,緩緩變形,正要對我攻擊。關於世界是否真的趨向毀滅,我一直漠不關心,然而當時的況味竟有幾分末日之景,我將被我當時的愛人所弒,亦懶散倦怠,了無生意。
過了一會,我在同個街頭看見小說家經過的身影。
※※※
世界充滿晦暗的幽影,惶惶分裂。
原來,小說家一直還有邀她出去?
不對,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像罷了。
回到狹小的房間,暗影之室,我想到小說家的新書叫做《長夜未盡的緩慢之島》。這本我一字仍未讀過的小說,有個哀戚又象徵意味濃厚的名字,亦如此夜漫漫迢迢。
我翻開筆記本,寫下寥寥幾句:
『即將分離,不要害怕;沒有血肉,就不會痛苦。反正我總是看不清楚,玻璃反射的臉面總是虛假,不用擔心自己無法承擔。』
我是高克明。
不,
我是吳十艾。
【羔子】
台北人。喜歡從男孩的視角來寫,也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也寫女、慾望、生活。
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lamblin.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