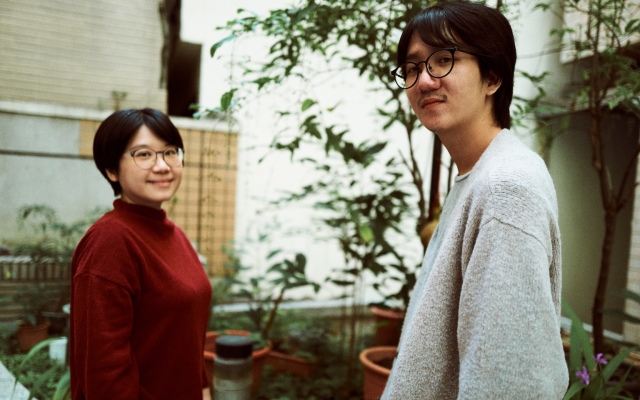演到矯情,最後只想躺下來——專訪陳栢青《尖叫連線》
「欸妳看我這個心臟噴血可不可以啊?有沒有很符合妳要的主題?周湯豪也穿過同一款喔。」他抵達專訪現場後馬上指拍攝要穿的白襯衫,想確認自己是符合需求的。
坐定先整理好儀容,手機屏幕當鏡子,頷首微笑,此角度有助瞳孔變大,鏡子裡自己變得滿可愛。陳栢青的手機備忘錄裡記滿了時間管理、自我管理、有錢人為何要使用長皮夾、賣長竹竿的人為何永遠不會失業、色彩魅力教你精彩一生等筆記,「我觀察別人,努力模仿別人,我想知道如何有自信,這世界我看別人活的都是高清全彩 1080p,我自己卻只有最低畫素。」
一邊用手指梳整瀏海:「我去演講超不爽,現在受訪也超不爽,我本來今天要理光頭來表示我的不爽。」不爽書市怎麼這麼爛,寫了好久沒人理,沒人愛我了嗎?「我好可憐喔。」每天醒來的惡夢是刷博客來即時榜,害怕沒有自己。更害怕有:「那我還要繼續擔心多久?還不如給我一刀痛快。」快來愛我是陳栢青永恆的潛台詞。
陳栢青演得駕輕就熟,扮裝獨角獸、艾莎、程蝶衣、黑山姥姥,騷底出身,別人覺得他就是那種 drama 系演員,把造作合理化,出糗就可以被看淡。
The Fucking World
散文集出版四年以後,陳栢青推出第一本純文學跨越類型的長篇小說《尖叫連線》,全文十七萬字,恐怖為外框,夢中夢的輪迴結構,國家計劃底下、病毒肆虐、揚言拯救台灣的人類卻爭先恐後求生。「之前好朋友買我的書說都看不懂,這本想為大眾寫,我希望我好朋友也看得懂,所以用類型當出口,內核是純文學,故事更通俗⋯⋯」在陳栢青認為文學提出問題,通俗則給問題一個簡單的答案,「但寫完發現,這下自己成為問題、給讀者製造更多問題了。」
陳栢青是喜歡鬆綁框架的,因此這不是典型的文學、也不是常見的類型:「我本來想做橋樑,沒想到純文學圈說太類型,類型圈說踏馬的根本看不懂,哎我不是說這其中誰有問題,我是說在座各位全都有問題。」前一秒佯作生氣,下一秒笑得慈悲為懷:「不是啦。讀者們唯一的問題,就是需要寬容。再給我一點機會。也給彼此機會。你不要逼我做選擇,但你可以選擇我。」momo 購物台的兜售語氣。
.jpg)
小說充滿恐怖片彩蛋,暗藏類型解謎樂趣,比方夢中夢結構來自《半夜鬼上床》層層夢境的無限死亡:「我去演講問讀者說欸你們知道佛萊迪嗎?他們就說『yah!時代力量』,不!是!不是那個佛萊迪,雖然他也是鬼王。」佛萊迪可是八〇年代家喻戶曉的鬼王啊,他感嘆。
陳栢青解釋自己為何喜愛恐怖片,他說起小時候最愛電影的《金髮尤物》。女主角艾兒白笨美,自帶逆轉勝光環,他詳述劇情艾兒抱怨被男友拋棄,美甲小姐邊做指甲邊說:「嘿小妞你不是最慘的,我比你更慘了,我被男人拋棄了,連狗都無法帶走。你是哈佛法學院學生,我只是高中輟學生,還有大屁股和妊娠紋,連你長得這麼漂亮都這樣了,我該怎麼辦呢?」
「電影裡艾兒第一次拎祖媽法律系就是幫美甲小姐奪回拖車,跟那隻狗。我的人生就是這個美甲小姐,而我的滿足是我想要贏回這隻哈巴狗。」
「美甲小姐抱著那隻狗,那隻哈巴狗長得真的非、常、醜,她跟那隻狗親嘴,我甚至以為他說的是:『謝謝,這是我只能夠擁有的了』。每次看到這橋段,我都會哭。可很多年後,我忽然明白,我哭並不是因為我以為自己是那個只要努力,就有無限可能的艾兒。而是因為,多年前我就在美甲阿姨身上看見自己的命運。我哭是因為,那才是我,被男人拋棄了,連狗都無法帶走。有大屁股和妊娠紋⋯⋯」他寫出歪斜醜怪的角色,每一個都不正常,每一個都至少是真的。
對恐怖片的認同也在被賜死的 B 咖:「裡面的那些 bitch,那些一定會死的角色,我好想讓他們活到最後⋯⋯那就是我們啊,恐怖片裡 gay、黃種人、做愛的人,一定會死。我們是規則裡一定會死掉的人。」寫小說,把這些人撈回來。
「你不想當主角,那你想當什麼?」
慾望。
——《尖叫連線》
小說裡,陳栢青讓角色沉沒於高壓電流通電的大水中,臨死前對世界比一個中指,致敬《魔鬼終結者》裡阿諾史瓦辛格,I'll be back:「我後來覺得,我人生最後沉到電漿裡面,就是要比中指,終結者比大拇指說 I'll be back,我要跟世界說 fuck。憑什麼讓人們受苦這麼久,操你的世界^^」
.jpg)
那些怪物,都好耀眼噢
《尖叫連線》收納經典恐怖片角色,不人不鬼,每個角色都有一場變形記,在校園裡展開求/逃生,勾心鬥角,殺死與等待被殺死。同儕間的霸凌源自陳栢青童年,「小學碰到討厭的、欺負我的人,就會想叫他去死,希望他上學路上被車撞、上廁所掉到馬桶裡、從高樓層把他推下去,我會想各種奇怪的死法。」
在小劇場裡懲處用刑,直到長大回想,劇本裡有時會有超展開——「我會幻想到,他掉到下水道裡,十分鐘後我跑去掀開那個蓋子,問說『哈囉有人在裡面嗎、我好像聽到聲音喲,我來救你!』或是他摔在路邊快斷氣,我過去幫他人工呼吸,心跳噗通噗通因為是跟帥哥接吻⋯⋯」
「那麼,這些人就會想跟我當好朋友。」
既恨,又渴望。「我多想跟對方待在一起,可憐吶。我詛咒對方,靠著這個活下來。」讓別人死以後,開始想去拯救、被需要。當善意被傷害誕生了惡意,再用善意來掩藏:「這就是小說誕生的片刻。」
「就算他們無比討厭我,我還是會覺得天啊他們好耀眼噢,他們身上有一種光芒,是我一生都想觸碰到,無論如何都好想成為⋯⋯我是這樣成為怪物,怪物身上有我渴望的東西,但他們都是快龍了,我好像只能是進化到一半的哈克龍。」
高中跳健康操,全校面前被點名帶操,「他就會故意挑你出來,因為你就是娘娘腔,做操起來很娘很好笑,你嗲嗲地喊一、二、三、四,全校就會笑成一團。」他稱這是不露痕跡的高等霸凌,從精神上控制、讓你懷疑自己有問題。笑自己格格 blue:「對,我就是這麼娘,這麼醜,我就是害怕出錯。」他曝短的時候居然也像信心喊話。
後來陳栢青就練成一身演技,「跳完健康操下來,我會假裝我很好我沒事,下來還要笑笑說哎呀怎麼跳這麼爛呢呵呵!」假裝自己是故意跳爛的,別人會以為上次他也是假裝。什麼時候真出糗真羞恥,誰也無法辨識。「我學不會面對出糗的瞬間,無法坦誠,但既然分出不來什麼是真的,不如讓一切都是演的。」
「我覺得無法控制是非常羞恥的,所以我致力於打造國王的新衣。」因為這樣彆扭地保護著自己的真實:「柔軟的地方好像也被破壞殆盡,本來應該像白石一文《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我卻被自己奇怪的保護方式弄壞了。」
我心中尚未被填滿的空間
小說裡設定「掃具櫃」中藏了霸凌遊戲的謎底,陳栢青偏愛狹小空間,在《大人先生》也寫過自己對廁所的執迷。「我的世界好空曠喔,我想跟別人很靠近,我很羨慕大家可以很親密地在一起。」
問他小時候比較常跟女生還是男生玩?「我沒有跟任何人在一起玩,我國小就沒有朋友。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人可以在放學時跟我說:『我們一起回家吧。』」放學時間,陳栢青刻意慢動作收書包,等人來找他,「我會故意忘記東西再走回教室,但還是沒人跟我說。」不過,他也沒勇氣跟別人說一起回家,因為害怕被拒絕。如此推拉的厭煩,「哎我就蔡壁如啊⋯⋯」
他最愛的空間是「腳踏車後座」,陳栢青露出甜蜜臉,「一個人在前面,另一個人從後面抱著他,臉頰只能貼著他的背,這是全世界最緊密的距離~~腳踏車開始往下騎,就一直蹦蹦蹦蹦碰到那個背,多希望路有無限長,腳踏車可以一直往下騎下去。」他怨恨 Ubike 2.0 ,車體設計沒後座根本剝奪了他愛的機會:「我要連署!敦請柯文哲至少在 Ubike 上搞個火箭筒出來!」
又他寫自己獨處的密閉空間,直指躲在櫃裡的安全。「小時候看《白髮魔女》,裡頭有個魔教教主姬無雙,他其實是一對連體的姊弟,但背心貼在一起。兩面都是人。電影尾聲,他被一刀兩斷,那個弟弟說:『原來,能夠躺著睡是這麼地舒服。』」姬無雙出身就有畸形身體,成了棄嬰,仇恨讓他變魔鬼,歇斯底里殺無赦,後來他求愛時遭主角殺死,終於看到了自己連體了另一面,他癡醉想,終於不用牽掛了。
「你不用再擔心你的背後了,在櫃子裡,不用擔心背後,背能夠靠著後面,多讓人安心啊。」

實在太寂寞了
姬無雙有令人畏懼的外表,因此他一生都孤獨,為了掩飾孤獨,姬無雙穿上兇殘的外衣。小說裡,每個人物都是演員見習生,努力穿上角色的衣服,那也是陳栢青。「我之前去《洛基恐怖秀》扮裝,發現我裝成女生,反而是我最 man 的時候,我故意壓低嗓音、腿可以開開。雌雄同體,覺得同時把握了男和女的元素,演到某個極端,反而可以調度。」
「演」的時候便安放自己,先自嘲我就是假掰,底線打開了,誰還能作弄他:「但有些人能演到一個不知道自己是在演的地步。他們會得奧斯卡,在人生裡拿小金人,無往不利。比起來我不過在演搞笑短劇。」演是保護,但小說中時常有上帝視角出來說:「騙你的。」像中島哲也《告白》用一瞬間拆穿漫天謊言,這也是他所恐懼:「我總覺得,能夠騙到最後就是愛,你都沒有揭穿,別人也不知道,對那個人來說就是真的了。」
「只要順著別人的話說就可以了,把自己暴露出來多難。我發現人們並不是真的想要對話。有時他們只是需要有回音。」他忍不住誇張,慣性說謊,但道亦有道,善謊者自帶真理的眼睛,也容易發現別人說謊:「這時候請你別拆穿他。」
陳栢青納悶的反而是,為什麼這個時代期待我們每個人有張萬用的臉?
「現實世界你面對不同人有不同張臉。不一樣的口氣和分寸拿捏。我不信你和朋友打屁聊天那張屁孩臉會和面對爸媽時一樣。世界曾經是錢包裡的金融卡,你自己根據需要和紅利點數選擇要用哪一張。但現在面對朋友、面對整個世界,那張臉就像 Apple Pay,一卡刷全部的機器,可是真的是這樣嗎?」為了說悄悄話、打造那張萬用的臉,開小帳、申請分身 ID:「網路世代人們多痛苦,都在經營幻想的藍勾勾,這件事費盡了我一切力氣,我已經撐不下去,如果他們發現我 Apple Pay 拿出來刷不過時,消費者會有多生氣?」他把自己想像成商品。
發願貨出去人進來:「但我無法處理這些不同卡片的匯兌關係。」朋友有時黑特他,也有人說他假。「可如果用同一套標準面對每個人,對方真的承受的住嗎?別人愛你,你要誠實。你愛別人,假做真時。」
他說,好累啊好想逃跑,也曾跟神明發願如果寫作能寫好,這一生不要愛情不要任何友誼。斷念死灰。幾度和現實斷線,刪除過臉書和一切交友 APP,並拿出 Nokia 3310,但不到兩分鐘又用回智慧型手機,帳號重新申請回來。幾秒種檢查一次訊息欄位,有的時候手機鬧鐘響起,他會假裝是有人打來找他:「喂?」
實在太寂寞了,好想跟別人說話。
(1).jpg)
美肌的我,低畫質的愛
一邊拍照的時候陳栢青說:「拜託幫我修修臉唷~~推推。」
小說寫自拍與美圖秀秀,反凝視,美肌再美肌。「我覺得自己活在美圖秀秀裡,我想看久了修圖,誰都會不習慣真的臉了,有時我覺得我們為了活在那張臉裡面會用盡一切,不然我每天晚上敷臉幹嘛,誰不是活在表演裡?」
陳栢青認為自拍和寬容很像,「自拍的時候你會發現畫素比較低,手機前鏡頭畫素都比較低啊,用前鏡頭檢視別人,用 4K 的畫質看別人,多嚴厲啊。」手機前後鏡頭不就是「存在」的隱喻嗎?「大家都是用前鏡頭補妝,低畫素是你的粉底,預先幫自己打底一次。誰都這樣縱容自己。高清反而無法靠近你自己,太嚴厲是活不下去的。用主鏡頭看自己,反而覺得自己是別人,跟自己裂解開來。」
美圖秀秀自拍,濾鏡磨皮,連吃個食物都要 Foodie,拍下「生活」最飽合與穠纖合度的樣子,在#selfie 自戀文化裡:「自傲不也是自卑的一部份嗎,最大的驕傲就是最大的憐憫,夠對自己自憐才能自傲。挺起胸的同時你就會憋下肚子。」
「我的存在薄得像一張紙。」以型補型,於是這一年他讀最多的類型是:「魅力怎樣打造?好感說話、銀座媽媽教你如何與人相處⋯⋯。洗手拜讀,像是新世紀的十戒,真的會照著做唷。」結果呢?只是越來越歪。像是跑錯舞台的演員。「分不出來舞台前後了。」,誰都看得出他一臉窘迫的臨時演員模樣。「所以,不要讓別人發窘。那是真溫柔。」
於是他在小說裡從假演員變成真上帝。打造自己,知道自己被看著,卻是為了去看到:「我們所有的看人都隱含了被看,所有看人的方式都是想被看見。我一直很想找出鏡頭後面的眼睛,是誰在看我?寫小說的代價就是要不停地看人,那你就不能不意識到自己的眼睛。」
.jpg)
你不(只)是受害者
《咒怨》裡的俊雄被父親殺死,怨念籠罩屋子裡的訪客,惡意傳染;《七夜怪談》貞子被殺死丟進井裡,恨意深植在錄影帶,電視機裡貞子的眼珠怔怔在看。這些加害者,都曾經是受害者,陳栢青將原型鏤刻與延展,還魂到小說,讓鬼再活起來。
小說裡每個人都同情又厭惡自己,每個人都搶做受害者,陳栢青告解:「我忍不住想揭破這一切,這個時代最有利的就是扮演受害者,所有人都說:我最可憐!沒人會覺得自己是加害者,我想用小說指著你,沒有,你只是在扮演受害者。」同時指著自己。
「如果有一天,我選擇不自憐呢?我想從這個問號裡面獲得力量,我之前都在逃、受委屈、裝小媳婦,如果有一天我可以說:甘阿捏?那我可以獲得什麼力量?」說的也是網路正義,講究正確,沒有容錯,狹持正義就能鍵盤殺人。
正義的悖論,小說情節裡角色想拯救在意之人、最後卻害死他:「我們的愛就是會殺死別人,這是我現實上的困境,我就是會搞砸、弄壞這一切,我像一個詛咒。」陳栢青以為抱持善意、自憐自憫,不就是最現代的怪物嗎?「一方面恨鏡中的自己,一方面覺得天啊鏡中的我好可憐啊。這就是『自己』的誕生啊。」
從《大人先生》來到這裡,每次轉大人都失敗,但他沒放棄努力成為一個大人,也許是意識到更年輕的讀者,從閱讀裡可能開闢逃逸空間,「但是,不要絕望喔。至少,你們可以在這本書裡,稍微喘息一會兒。就算身為怪物,你也不是孤獨的。」他寫也想造橋鋪路,勝造七級浮屠。
自省的態度放入結構,小說同時具備三個人稱,有被害者、受害者跟旁觀者的觀點:「在所有暴力關係裡,最恐怖的是加害者嗎?旁觀者其實也很恐怖,你就是在看著這些傷害發生。」陳栢青說自己作為小說的寫作者,就像韓國電影《殺人回憶》最後一格畫面定格在宋康昊的主觀鏡頭,觀者也可能是兇手。
從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觀點轉換,跳脫了「自己的身份」。「自己」在小說裡透過全知觀點拉拔出眾生相。小說透過直播談當代政治關係與權力運作。故事裡俊雄從 101 屏幕裡爬出,陳栢青想到小時候看完《七夜怪談》於是用布掩蓋電視機:「上個時代我們害怕貞子爬出來,這個時代我們想要走進螢幕裡面,我們都想變網紅,反而是貞子要尖叫了,一堆人要湧進她的螢幕裡。」
站在自己的命運之外
寫螢幕養成的一代,「導演」一角在小說敘事中不時跳出來,製造罐頭笑聲、有時喊卡、有時畫外音,他以為「我們終究失去第一手的經驗」:「沒有所謂經驗的處男了。文明即預言。現代社會的便利就是預約。於是我們失去所有的第一次,電影、電視告訴我們一切,美食到穿搭,愛情到失戀,第一次初吻心臟激烈狂跳,該不自禁的閉起眼,或是失去時繞著操場瘋狂奔跑⋯⋯這一切,影像媒體全告訴你了,你會覺得自己經歷過了。我們的初戀,被世界偷走了。」
直到人們能將現實也當作電影——直播鏡頭與導演指令傳遞全知觀點,世界教會人們旁觀與冷淡。《尖叫連線》用直播和各式影像媒材逼視光怪陸離。說的也是作品外的他。他也曾是故事裡冷眼旁觀過霸凌現場的人,他也是為了不讓他人一起被霸凌、推開拯救者的人。自陳懺悔,「至少我還可以寫小說,可以去保護別人。」
.jpg)
陳栢青也設定星座運勢在小說中推演劇情,「我們這個時代的上帝就是 唐綺陽啊,妳寫的時候要空一格唷!以前我們看瑪法達,現在看唐綺陽。誰不相信算命,『更上面還有絕對的什麼?』,只是今天我相信的,是雲端上方有一個白鬍子的老傢伙操控一切,而其他人把這一切交給電視機、股匯市盤面、政黨黨魁或是至高領袖,比起來,我的嗜好善良而無害多了⋯⋯」
善良總是昂貴的。陳栢青花很多錢在算命上,「所以你們不該買書嗎!」他不忘提醒。但這樣說來,算命也是某種寫作吧,寫作者不就是站在角色的命運之外:「所有的寫作者應該都很愛算命吧。我覺得那很恐怖,聆聽某個至高者揣度著你,根據你的一切,運算某個系統,去決定你的下一步。人物設定、情境、背景、性格決定命運⋯⋯算命聽著聽著總像跟另外一個同行在過招。」用上帝視角看運勢,命不是我的,就不那麼慌張了。
.jpg)
算命卜出生命的來去,很想確認好自己,或許也是怕活著活著,有人冷眼告訴他一句:「騙你的。」
讓角色互相詐欺、互相保護,陳栢青說一直說謊,演技訓練是為了終有一天被拆穿:「我想要你看見,我是演的,我是假的,我在說謊,我好想說、哈哈被你抓到了啦,你快抓走我吧。」陳栢青伸出雙手,做出想被逮捕的樣子。
「我假裝扮演的這一生,就可以放下了。我不用扮演怪物,可以像姬無雙一樣終於躺著睡。」
離開前,陳栢青換掉了那件心臟噴血的白色襯衫,那其實是一片由紅色亮片所組成的血跡,採訪前我們說要拍陰暗一點的,他依然閃亮登場。
說謊為善,宮鬥求生,演到矯情,最後也想躺下來。
《尖叫連線》
作者|陳栢青
出版者|寶瓶
出版日期|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