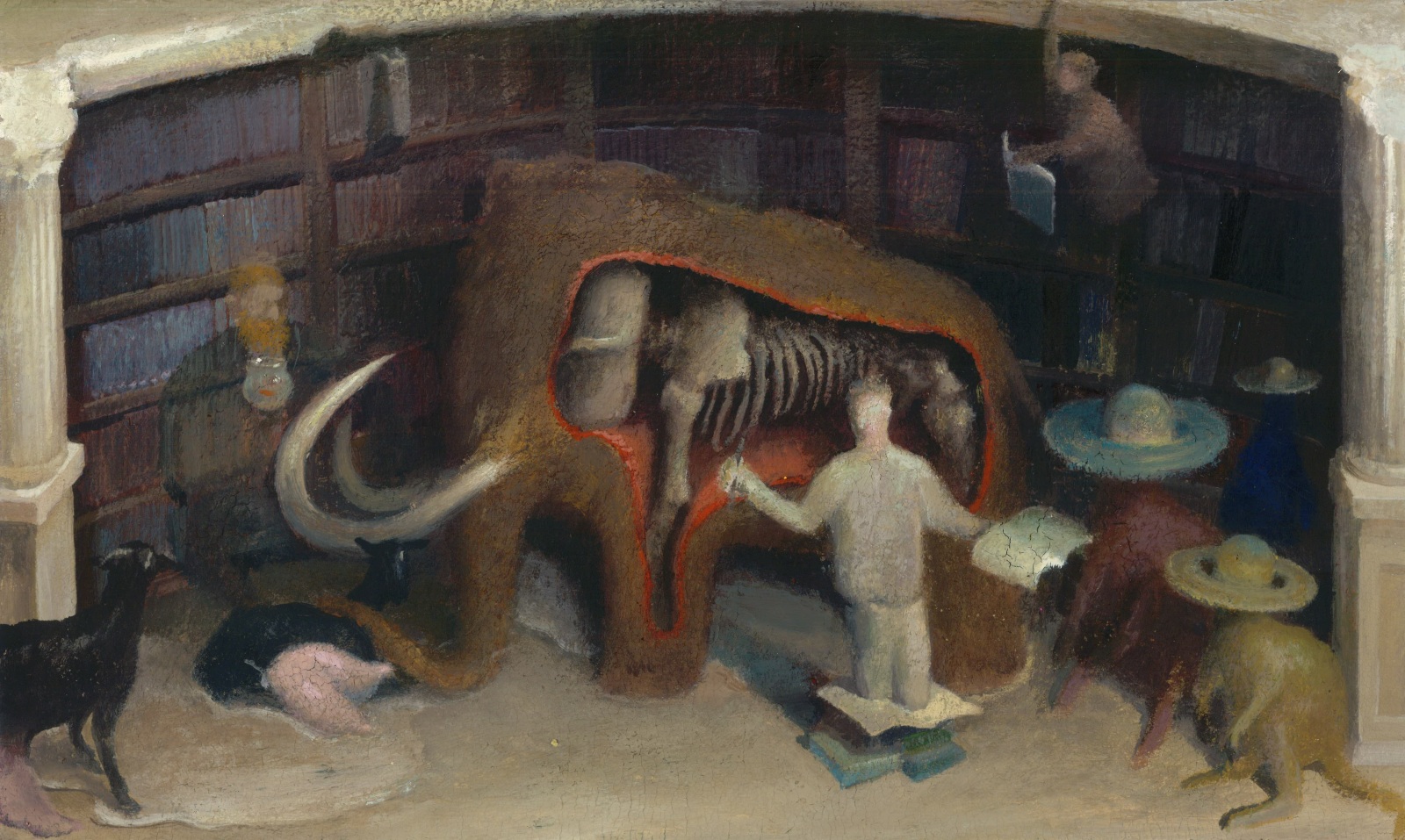
不痛苦的文學是什麼樣子?專訪包冠涵:寫一座火山,給沒有跳下去的自己
四月,今年第三個人從勤美誠品 11 樓一躍而下,被發現倒臥人行道後送醫不治。原本因為二三月連續兩起墜樓事件,商家已加裝防護網,沒想到被女子以美工刀割破。
二十出頭的包冠涵也有過衝動。靜不下來,一台摩托車到處跑,每過一段路口就抬頭,望著高樓想:從這裡跳下來呢?那裡呢?跳下來會怎麼樣——
出書後發表會辦在線上,對談人張亦絢說探討自殺時,方法往往比原因更像原因,會指向一種戲劇性與語言,有如占卜:上吊是因為痛苦沒被看見;服毒是自認未受到照顧、把毒藥當成藥;而跳樓,是活在世上失去了自由,無法任性。
包冠涵傻笑說,滿準的。
「跳樓是你把自己化作一滴眼淚,然後墜下。那代表你有一種真正想說的悲傷。也許我每次看著頂樓,想像自己往下跳的時候,我都在試著哭。」
10 年前出版的中篇小說集《B1過刊室》有走入海中的敘事者,《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則有人墜落,不跳樓但跳火山,火山口跟勤美誠品一樣裝上防護網,結界般分離了生死,生者卻想搞懂死者為何非得要死。
他說這不是一個自殺故事。
我好討厭這裡
熟人叫包冠涵包子。周芬伶在他第一本書《敲昏鯨魚》序裡寫,包子讓她想起王文興、黃國峻、一點點七等生,除了文字風格西化外,「躲在文學的國度中雕刻文字,只與自己對話」並且「沉默而近於自閉」,還因為都穿牆壁色系所以與牆壁融為一體。
以上都不是包冠涵的初始設定。
小時候家在南投,放學後會跟同學玩鬧、結伴打球,汗水的童年金光熠熠。直至高中搬去台中,忽然來到都市的位移差,讓他漸漸無法融入群體。為了逃避社交,下課他都待在福利社,折返後剛好打鐘;或熬夜整晚讓自己累垮,趴睡才能理直氣壯。
某天班上同學揪團唱歌,大寫的 CULTURE SHOCK,「我從來沒有唱過歌,也沒辦法想像對有一群人來說唱歌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包廂裡,眾人高歌而他沉默——把手伸進書包,摸裡頭一本鄭愁予詩集。「我不敢直接拿出來看,我就偷偷把手塞到書包裡去摸。」護身符一般。
不過,開始寫作還得等到大學——說來那段日子曲折,起先他厭惡學校、根本不想去,退學通知一直來,一間換過一間,先是亞大外文、然後是東海哲學,再轉去中正成教,流浪半個台灣又被退學。
問他為什麼那麼討厭上學,他笑了出來。「村上春樹有一本小說,主角也問過另一個角色同一個問題。」那他怎麼說?「他說,他很不喜歡中庭除草的方式。」
這包冠涵太懂了,「我去過某個學校等口試的時候,看到風把走廊上一個垃圾桶裡的垃圾袋吹出來,欻欻欻吹走,我就想說天啊——我好討厭這裡。」
彼時他原本打算輟學後直接當兵,碰巧發現東海在招生,朋友勸他去考考看、沒上再當兵也不遲,「我想說,好吧。」
但若不是這晃蕩四五年後的姑且一試,他也不會剛好在那一年踏入東海中文——那一年,是周芬伶首次開設創作理論課的那一年,他的同學包括還沒寫出《花甲男孩》的楊富閔、還沒寫出《女子漢》的楊隸亞。
回憶起來,細節如宿命。包括在圖書館遇見那一本郭松棻。
黃色封面、楷體字,前衛出版的《台灣作家全集》其中一冊。現代主義、左派、政治恐怖、苦難的風景,刺入他的視野。這就是文學。「寫太好了——我那時候只是天真地想說,寫太好了,我一定要拜託他教我寫作!」
渾然不知郭松棻幾年前就死了。
When We Were Orphans
無法拜師郭松棻,頭頂燈泡一亮,「不然我就去唸研究所,研究他好了!」事後回想真不是個好主意,申請上中正台文所的他,兩個星期就被打回原形,「⋯⋯什麼鬼,不想去唸。」
老師年輕開明、教學認真,但就是不想去。
不去學校的時間,騎車、抽菸、談戀愛,之外就是寫作了。
第一篇小說始於亞大宿舍的窗台,「我在窗外看到了一個滿漂亮的女生,內心就充滿了一種慾望或動搖嘛,我就忽然意識到,如果我這一生,都要不斷地被各種美麗的東西或是痛苦的東西侵入,動搖我這個人的邊界,那人生有點艱辛。」
小說叫〈甜刀刃〉,主角會在某一瞬間聞到甜味,失去意識,把眼前的人的皮膚與器官拆下來,做成首飾或配件。重讀這篇他只想鑽到土裡,但又偷偷驕傲:「那好像是第一次,我覺得小說跟你的內心可以有種對應的關係。」
還有個習慣是把寫好的小說列印出來,給朋友看,觀察對方表情,「一般我寫都是一些好笑的小東西嘛,他們可能就會笑一下,我就會得到一種快樂。」一種脫口秀演員式的快樂。
「好笑的小東西」蒐集成第一本書《敲昏鯨魚》,朱少麟盛讚「極亮眼的新生代作家」,然而作品沒有轟動文壇,賣完就絕版;幾年後《B1過刊室》也是類似下場。兩本書悄悄堆積讀者心裡,上網一搜書評零星,他不曉得都是誰在讀。
或許有點孤單吧。
兩本書裡有好多動物,沉默的動物、唱歌的動物、話講個不停的動物。《敲昏鯨魚》同名短篇寫王大頭養了一隻會唱歌的鯨魚,好不容易受同學簇擁,鯨魚卻被偷;寫進小說的第一隻動物是〈鱷魚〉,不男不女,讓人傷心,靈感來源邱妙津。
其他筆下動物包括但不限於:長毛象、山羊、老鼠、大象、兔子、蛞蝓(是個教授),最迷人的是《B1過刊室》裡一隻讀中文系的馬來跗猴——
我低聲對馬來跗猴說,你有沒有注意到,當傘收起來的那一瞬間,會有一種很美麗的聲音,我不會形容。馬來跗猴回答我:你什麼東西都不會形容,因為你笨透了,而且你這輩子不可能懂得什麼是美麗, 你不應該使用你不懂的字眼。
.jpg)
「我覺得只要動物出現了、動物說話了,它的第一個意義是『這不是這個世界上會出現的事』,不會有人誤會這是關於這個現實世界的小說。我首先依靠的是這件事情。」
但也因此,「這些動物都是一些孤單的動物。」
「牠除了你的現實之外,也不屬於別的地方,你們兩個其實是在一個異世界裡,共有某種親密跟孤獨。石黑一雄有一本小說叫《我輩孤雛》,標題的原文是 When We Were Orphans:當我們過去是孤兒的時候。」
孤單的人,召喚出孤單的動物陪他,一起孤單就不算孤單了吧。
我們都需要傷口在那裡
周芬伶曾在序裡道破動物是他的掩護體,掩護真實經驗的赤裸與脆弱;然而更精確來說,掩護他的是虛構。《B1過刊室》第二篇〈Chen Yun Zhi〉中,創造了一篇網路流傳的〈為另一半口交技術完全手冊〉,他寫了六頁口交,如何「在不至於會窒息的情況下儘量讓陰莖深入口中」,深喉嚨是一件有詩意的事。他散文寫不來的事。
但常常邀稿單位都請他寫散文,「每次不能虛構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怎麼寫起。我的發聲位置在哪裡?我要去哪裡講東西?我好像需要一個可以虛構的自由才會想寫。」
怎麼樣的自由?「那是一個很好的狀態,因為每個人心中的真實——你心中的真實跟我心中的真實,對我們的生命來說都是一個極權,我們都不得不去服膺。可是文學,尤其是小說,有一種可愛,它可以短暫地繞出你靈魂的真實——那個掌控著你、把持著你的真實,去虛構,去挑釁。」
虛構是種民主。
前陣子與九歌總編輯陳素芳筆談,寫到一半麥當勞叔叔站起來,「他瞥見我在瞧他,對他眨了眨眼,踩著他的大紅鞋子來到我身邊,請求我替他保守這個秘密。」採訪前信件往返,聊到他喜歡的咖啡廳,「有時候客人很多,幾乎擠滿整間咖啡店,我的左肩會站一個客人,耳垂上也掛一個 XD」
他不認為袒露與其相反,反而,好好地虛構是好好地誠實。
《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是這樣一本書。在火山口旅店當房務員的杜有恆,遇到小女孩阿福與單親媽媽劉映珊,阿福想知道外公為何在她出生前一年跳下火山。角色的傷心與快樂重疊於作者,寫的時候他告訴自己,要袒露到「就算受傷也沒關係」的地步。
小說的袒露並非將經驗複製貼上,而是捏塑出角色的身世與命運後,連上自己的感知。包括痛覺。父親自殺後劉映珊一直沒哭,某次登門的客戶是對雙薪家庭小夫妻,她發現自己竟想把 iPad 搶過來拗斷。「你真的會悲傷到你再也沒辦法應付日常,但你還是得生活,這是最痛苦的時候。」
最痛苦的時候,包冠涵曾拿菸頭就往手背上燙,「那個菸頭大概有幾百度吧。」
他一邊比了動作,「超——痛!」
「我背棄了我的身體。」他著急起來,「那一瞬間我真的非常非常後悔。我覺得身體是獨立我的一種存在、跟我的心智是平行的,我不應該去傷害我的身體。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袒露傷口,也借角色之口叮嚀自己。修鞋工 Jack 說:「即使那只是一雙他媽的 Timberland 破靴子上的傷口我們都需要傷口在那裡,它會提醒我們該怎麼樣去對待一雙鞋子、一個身體、一種人生。」
有次杜有恆在雨中騎車打滑,西藥房老闆娘盯著他受傷的膝蓋,以鑷子挑出爛肉裡的碎石。嘴中唸唸有詞:「我會幫你清洗乾淨,讓你好起來,過程會有點不舒服,你要忍耐,好嗎?」
杜有恆後來發現,這些話不是對他說的,是對他的傷口。
贗品
寫作,也是包冠涵在對自己的傷口說些什麼。有段時光,早上醒來不想睜眼,清醒了就騎摩托車看高樓;小說寫到凌晨兩三點,肚子餓去超商找吃的,街巷極黑,抬頭一看星空燦爛,「我只覺得很孤獨。」
想死的現實裡,是虛構讓他活下來。
他開始寫中篇小說,不受限於短篇要能精巧、長篇要能延展,中篇的份量剛好可以把痛苦的生活寫成幻想,把憂鬱與慾望寫成另一個自己——把真的寫成假的,好像真的就不痛了。《B1過刊室》如此緣起,「這是我對文學有沒有辦法承擔人類痛苦的一個質疑。」
那麼,寫作於我而言是什麼?寫作是不義地對待心中之臉,而後在世界上散播不義的形式;寫作是一箇人狷傲地背棄自己心中因為負載他人之臉而生的種種痛楚,而進入一個有光的世界,一個受照物洋洋得意的世界。寫作從來只與生之欲有關。寫作拒絕負載生命真實的痛楚。——〈Chen Yun Zhi〉[註]
他做過一個夢,夢裡有一間空房,情節幾乎散失,夢醒來寫作卻變假了。
那段夢如神,在意志上方替他完成了所有文學,超越一切書寫,「如果那場夢是一個寫作,那我所有在白日、在清醒之下的寫作,就只是那個夢的贗品。」
「如果說一個夢可以以一種意象穿透我生命,那我寫作到底是為什麼?」
可是,寫作又幾乎是他的全部。
跟學校一樣,畢業後每個地方都待不長。拉開打工仔的履歷:加油站員、藥局店員、牛排館外場、架設舞台的工人、餐廳外場、咖啡廳吧台、教科書推銷員、手搖杯店員⋯⋯現在知道為什麼他的作品塞滿各行各業的人。
漫長工時的間隙,無時無刻不想著下一篇要寫什麼。「有一個畫面我印象很深刻,我在路邊,正對一個荒地,荒地上有各種雜物,垃圾啊、玻璃罐啊,破掉的網球啊⋯⋯我就看著那一片荒地,心裡有個聲音告訴我:只要我願意,我可以幫這片荒地的每一個東西寫一個故事。」
「那個時候的創造力或寫作慾望,是很直接、很豐盛,以一種力量蔓延過你整個生命。」
痛苦與寫作相生,彷彿跟惡魔交易。我問他,如果世界上所有傷痛都消失了,你還會寫嗎?
他說他本來以為會。
他目睹過那樣純粹而快樂的寫作啊。楊牧曾在《海岸七疊》的後記自述,從前不敢想像一個詩人能編出一本完整的快樂的詩集,但他做到了;當時楊牧剛步入第二段婚姻、兒子出生。包冠涵心想,如果遇上那樣明亮可嘉的一天,「我也有可能,單純寫一個只是快樂的小說吧?」
「——後來想想真的不行。」
以搞笑的節奏運行哀傷,但黑色幽默切開來終究是黑的,「我記得大江健三郎跟小澤征爾有一本對談裡說過類似的概念,說再快樂的閱讀,如果你仔細聆聽每個樂句與樂句之間的間隙,你都會感到一種悲傷。一種萬物與生命都在消逝的悲傷。」
《B1過刊室》完成後他瞧不太起自己,文字刻意詰屈聱牙,但晦澀又反向洩漏了自溺。〈Chen Yun Zhi〉中「我」自認被活著本身給扼殺了寫作,只想去埔里找個工作,過一份不再寫作、也不再跟寫作相關的生活。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人類有義務、正當性去承受這樣子的我。——〈Chen Yun Zhi〉
寫東西的熊
結束打工人生,戒了菸,今年是他在房地產公司寫文案的第十年。
工作安穩,很長一段時間他不太寫,但創作長篇小說的念頭一直在。是為紀念:憂鬱年代僅有的平靜是騎往科博館旁的敦煌書店,讀一整天,「長篇小說的特質是你會覺得身處在另外一個地方、一段旅程,你就在那段旅程裡安靜下來。」
曾大言不慚寫下「我感到文學是虛偽」的他,竟感覺被原諒。
幾年後收到雜誌邀稿小說,他才再度動筆。那是一個叫〈寫東西的熊〉的故事。失業男子應徵上馬戲團行銷,但團裡都是些不太正經的動物:高空飛猴、兩隻蟑螂、表演大便的羊,於是他決定找一隻熊加入,熊的特技是寫作,但沒人知道他在寫什麼。
「寫完,我覺得心裡有個東西活過來,有一種慢慢、好像又可以溫柔想事情的感覺。」他下定決心要完成一本長篇小說。
他首先建了個 excel 表格,每日進度化為實際數字,「寫長篇,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去哪裡、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那個過程很痛苦。有時候寫十幾二十天發現自己寫出垃圾,不可能繼續⋯⋯」表格便成了安心的印記:「再怎麼一無所獲,你知道自己至少有兩個小時是在寫東西,每一格、每一格就這樣子延續下去。」
包冠涵發展出一套儀式,如果不想寫,就要求自己提交一份檢討書。常見難題是情節推進之阻滯。他寫過一個老奶奶想找個地方等死,此地卻被一條西方龍盤據,於是組織騎士團討伐,但光挑長矛就挑了兩章,決定放棄。
又或《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雛形是一男一女在火山口對話,洋洋灑灑講了 17 萬字,也寫不下去。這些棄稿加總起來三十幾萬字,一概刪除。
直到小女孩阿福出現。
17 萬字裡是沒有阿福的。「某一天我坐在電腦前寫下了小說第一個場景⋯⋯寫著寫著就有阿福了。」
阿福想知道是什麼讓外公自殺,啟動了故事的速度。執著本質上是對母親的愛,「她其實非常清楚知道,他外公的過世從母親身上奪走什麼。有一段時間她是非常恨外公的,因為外公的死讓媽媽很痛苦。那是一個愛的執念。」
他說阿福是一個奇蹟。
追尋途中遇上許多歷劫之人,阿福打開了他們的嘴巴,多說一點,再說一點。包冠涵說這樣的寫作是一種傾聽,「傾聽也是一種創造,但把張揚的地方調低。我希望整個小說像夢一樣,有一種和緩的節奏,讀的人慢慢地走、慢慢地走,就把故事走完了。」
不要殺死我的火山
傾聽角色的聲音,也傾聽自己的。故事裡有一群人不滿火山口加裝防護網,控訴政策剝奪了自殺的權利,憤而組成「想死錯了嗎俱樂部」,部長小 P 說:他們想殺了我的火山。
小 P 國高中被霸凌得想死,抱著被子幻想自己沉到火山深處,被岩漿裹覆。小 P 說:「如果不是那個想像中的火山支撐著我,收容著我,我想就算我沒有真的去自殺,我也會支離破碎。」
光是知道自己還可以去死,就足以拯救人。

「他們是真的打從心裡相信可以死、有自殺的權利,生命可以比較好。我也常常覺得現代醫療的延命技術非常荒唐,比如灌食、比如葉克膜,生命一直被延長。這件事情非常可怕。」
前年爸爸過世,他去看了最後一眼。死前兩週爸爸昏迷,插高壓氧,「他變得很輕,真的像葉子。生理上還活著,但會覺得某個東西離開了他的身體。」
原本家人說好要送父親進安寧病房,聽說只要送進去,一拔管就走了,「好像是去買了十點的高鐵票一樣。」
原來死亡是可以預約的嗎?他曾幻想跳樓,但那樣不安靜的死法並非首選。包冠涵想過去外公家二水的山間自殺,「真的是很美的地方,它是一個小山坡,你爬上去之後,就可以看到鐵軌像夢一樣『咻——』滑過去。」
他想。他想開一台車過去,車子怠速時,一根軟管接在排氣管,另一端接進車窗的小縫,把軟管固定住,二氧化碳就會慢慢佈滿車廂,一點一點死掉。
在大片大片如光的綠色裡。
曾以小說延續想像,自殺者把遺書留在擋風玻璃上,「別人就可以先讀完那封信,再決定要不要看你的屍體——」他又傻笑,「因為我一直過不去的點是,有人會發現我的屍體,覺得很沒禮貌,不想把我的哀傷跟虛無放在那邊。」
亦是為何《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裡無人陪在外公最後一夜,「我不想要任何人用語言去破壞這個晚上,或是介入他做了決定之後那份孤獨的寧靜。」如同他的心願:「如果真的到那種時候,我不想有人勸我不要死。」
偏偏他捨得了自己、捨不得角色。
面對父親驟死劉映珊也曾想一走了之,杜有恆離婚又喪親後靜靜地潰爛,更別說小 P——但故事最後,岩漿依舊平靜,防護網依舊強壯,他們一起活下來了,「我希望這些角色在小說的當時當刻是安穩的,他們不會去真的跳火山。」
書名原本取作《容身的火山》:死亡將碎裂的生人接繫起來,每一種聲音、每一種語言、每一種生命質地都被火山所容赦——而這無關乎跳下去與否;對他來說,又或許是更加單純地,一個曾經找不到歸屬的人,寫了一個給自己。
這不是一個自殺故事,「我想講的是團結。」
後記
我問他,為什麼你出書從不寫後記?他不好意思地承認,怕寫爛。
「寫的時候,你的敏感度、你的開敞程度、你的集中度,遠超過寫完的你。有時候讀者跟我聊《B1過刊室》,我都想逃走,我沒有辦法再召喚出那個我。我只是一個蹩腳的東西。」
「而且我的小說應該會偷偷在半夜把後記撕掉吧。」這修辭很包冠涵。
他不只在寫之後感到渺小。「你有沒有逛過舊書店?台中早期有很多的二手書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全部都是書。我有時候就會覺得,寫作好像是一個非常微渺的存在,擠在一個大的空間,浩瀚像宇宙的空間——你只是小小地存在著。」
『渺小讓你覺得卑微嗎?還是舒坦?』「都有吧。可能舒坦比較多。」
寫作者自大過,但終是星塵的一份子。草屯的童年裡,家落在河堤上,他下田抓魚,丟石頭,試著丟到河對面。他說那是一個小小的地方。日子非常安靜,睡覺時聽見河水流過,「我覺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房間那扇窗戶正對天空,所以有時候我會打開窗戶、曬著月光。我人生有一部份安靜,就是從那時候建立起來的。」想起他寫:除了家那個小點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曠野。
後來還有回去嗎?他點點頭,但「房子賣掉了。就是去走走。」
偶爾。只是偶爾,他會想起那個小小的頂樓。小小的,不是讓人想跳下去的頂樓。天未亮時爬上去,看太陽離開地平線,割出了九九峰的輪廓,再一格格填滿田畝,最後停在他的眼睛。
現在還常常想死嗎?他說不會了。
註|《B1過刊室》〈Chen Yun Zhi〉一篇中,作者有意識在文句中摻入文言文用字及句構,其中包括異體字與簡化字的混寫,比如「個」與「箇」混用、「的」與「底」混用、「才」與「纔」混用,引用為尊重作者,以原作表記為依歸。[回到上面]
《柔軟的耳朵與火山上的歌》
《敲昏鯨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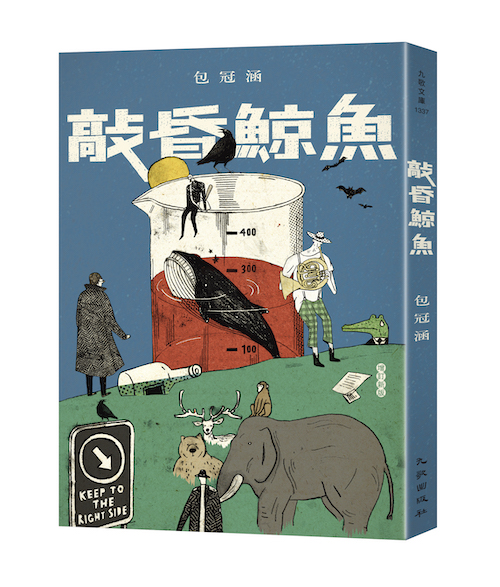
《B1過刊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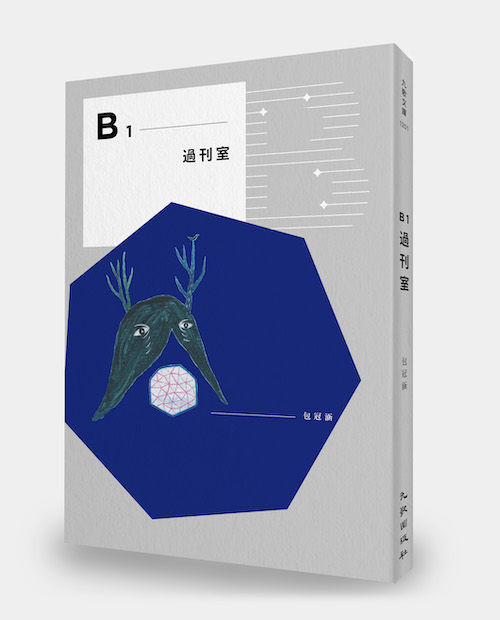
-%E7%AB%8B%E9%AB%94%E6%9B%B8%E5%B0%81.jpg)
-%E7%AB%8B%E9%AB%94%E6%9B%B8%E5%B0%8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