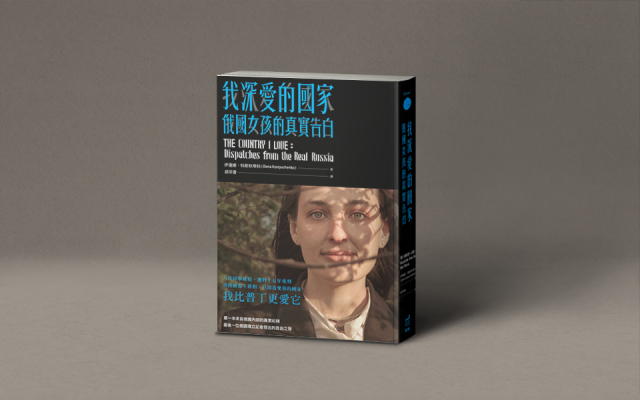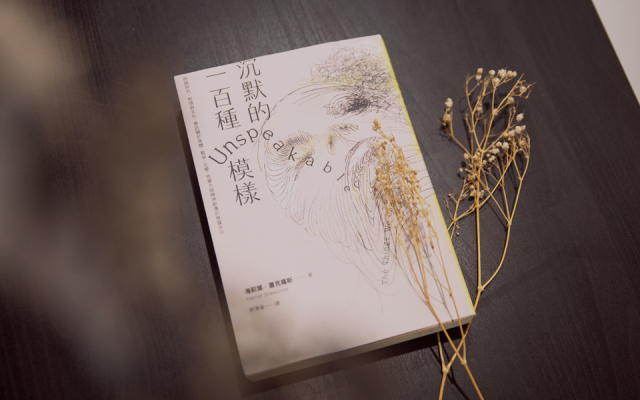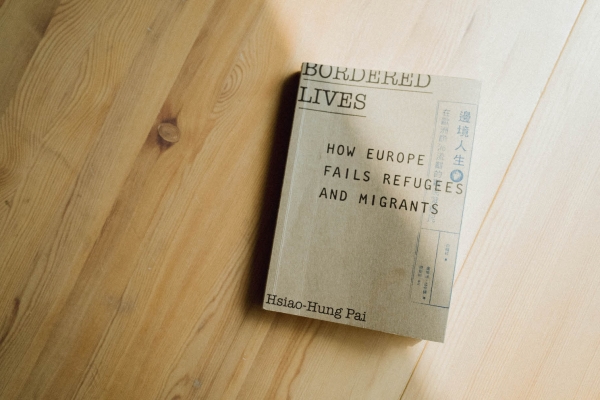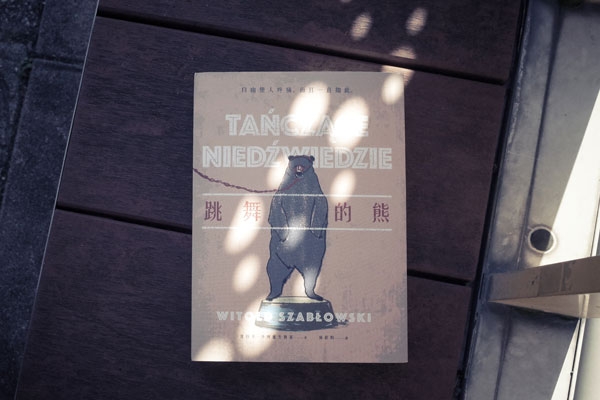從一塊烏克蘭人做的三明治聊起──專訪沙博爾夫斯基:在被分裂的歷史中,看見國與國的共難
波蘭華沙時間上午十點,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從打開視訊鏡頭的一瞬間就迅速進入了受訪狀態,絲毫沒有半點鬆懈。身為報導文學家的他,就連佯裝成寒暄的開場白都沒有掉以輕心:「所以,你問我剛剛吃了什麼早餐,也算是採訪的一部分嗎?」
正中紅心,好吧,也是沒有辦法。飲食是沙博爾夫斯基長期耕耘的主題,在台灣由衛城出版的《獨裁者的廚師》和《克里姆林宮的餐桌》,分別採訪了歷史上 5 位獨裁者身邊的御廚,以及實地走訪多位親歷過俄國與前蘇聯重大歷史事件的廚師,連車諾比核災善後工作的前線廚房也包括在內。而他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跳舞的熊》,在序言裡就將民粹領袖的空頭支票形容為糖果:「這些人把承諾包在沙沙作響的包裝紙裡,還假裝那是糖果。為了得到這些糖果,人們用兩條後腿站起來,開始跳舞。」
到了今年,他 2010 年完成的第一本書《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在台灣出版,原來早在彼時,食物就作為核心意象貫串:「整個土耳其被一道隱形的海峽撕成兩半。我的女性朋友早上和男朋友喝義式濃縮咖啡,吃可頌,談論世界文學。到了下午,她們戴上頭巾到外婆家喝土耳其咖啡。我的男性朋友會在夜店來杯啤酒,開心享樂。但喝酒的同時,他們唱的是兩百年前的歌。他們一副硬漢的樣子,不怕真主也不怕先知,但齋戒月一到還是乖乖禁食。」
話說回來,沙博爾夫斯基受訪這天的早餐吃了火腿三明治。這家麵包店過去在華沙並不存在,但現在來了,命運把烘焙師們從烏克蘭捲向了波蘭。他們原本在基輔經營連鎖麵包店,甚至在幾個城市開展了分店,戰爭爆發以後,他們逃離故鄉並在華沙重新開業。沙博爾夫斯基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食物如何在社會中運作,也如何聯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社會發生政治變化時,最先出現改變的,往往就是食物。
在《克里姆林宮的餐桌》裡,他曾描寫過一位遭遇過列寧格勒圍城戰的麵包師傅。她說,「麵包代表生命,維特多,在像被圍住的列寧格勒這種地方,你的感受會很明顯。打從在麵包店工作開始,我就覺得自己從原本的面向死亡,轉身面向了生存。」如今,從烏克蘭逃亡到波蘭的烘焙師,也許也共享著類似的座右銘。
𝑨𝒑𝒑𝒆𝒕𝒊𝒛𝒆𝒓・革命前夕的古巴麵包日記
沙博爾夫斯基自己也曾擔任過廚師,甚至是在丹麥哥本哈根工作。這是座連劇集《大熊餐廳》的星級主廚也得前往進修的城市,不過他在這當上廚師的理由,相較之下是一點都無法振奮人心:「我大學畢業時,波蘭正陷入了經濟危機,在那裡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失業率還非常高。於是,由於我在丹麥有朋友,我就去了那邊工作。」
在那裡,他當過人力車車伕,負責載觀光客去市區主要景點,邊介紹邊聊天。他也幫忙裝修船隻,在眾多斜槓工作裡,他擔任過墨西哥餐廳的廚師,同事們大部分都是來自伊拉克的庫德族人。
「天啊,廚房真是個神奇的地方,這裡充滿了故事,也充滿了講故事的人。」這與《大熊餐廳》裡分秒必爭(every second counts)的座右銘簡直是天壤之別。但反正這部劇集也不是叫大熊記者,裡面也沒有一頭跳舞的熊。
食物訴說的故事之中,也包含遺忘與家園。沙博爾夫斯基曾在古巴採訪過一位麵包師傅,他以前在米其林星級餐廳工作過,後來因為祖母的緣故回到了古巴。在臨終的日子裡,祖母向他抱怨說:「我的老天啊現在古巴的麵包真是有夠難吃,革命把我們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拿走啦,共產主義把生命的滋味都拿走啦。」於是,這位廚師受祖母所託,到處尋找革命以前的麵包配方,最後終於成功找到了一個四、五〇年代的食譜。
他原本只是為了烤給祖母吃,但是吃過的人都說這麵包的味道有夠好的啦。後來他順理成章地成了麵包店師傅。「這不只是一個關於特定家庭的故事,而是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故事。關於轉型,關於過渡,我想這是值得深挖的故事。」何只深挖,這簡直是一段可以銘刻在店裡牆壁上的起源神話故事,雖然有點太像知名新竹牛肉麵的況味。
後來,沙博爾夫斯基的創作主題都圍繞著轉型:古巴革命帶來的震蕩,就連食譜都無法避免;土耳其因獨特的地理位置,在冷戰時期左右不討好;波蘭等東歐國家在蘇聯鐵幕倒下後,人們如被訓練過的熊那樣開始掙扎著跳舞。不過,立志成為記者,那又是比古巴、比土耳其、比哥本哈根都還要更早的事了。
𝑺𝒐𝒖𝒑・什麼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
在十四五歲的時候,沙博爾夫斯基曾經讀過一個關於契訶夫的故事——大師開導新手的那種故事,文學愛好者的經驗主義神話——一位年輕作家帶著手稿去請教契訶夫,到底怎樣才能寫好一些,而契訶夫讀了年輕人的手稿後,跟他說:你確實有天份,也確實懂得寫作,但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只憑天份是不夠的,你必須先去生活。
青春期的沙博爾夫斯基讀畢後大受震撼,他心想,「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人,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作家。」先讓我們忽略 45 歲的他舉例時,所背誦的契訶夫故事,還包括了鼓勵年輕人去走私、偷竊以及坐牢。當年的沙博爾夫斯基這樣告訴自己:在開始寫作之前,必須先過一段值得書寫的人生。於是,他從華沙坐便車去了耶路撒冷,去土耳其跟任何一個願意聊天的人講話,去哥本哈根做各種各樣的工作。也許這就是值得書寫的生活。
如同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在〈什麼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中形容:「契訶夫想到的『生活』,是一種扭捏的混濁的混合物,而不是對諸事的一種解決。我們只要看一下他保存的筆記本就能理解了。實質上,這個筆記本就像一個床墊,裡面塞滿了他偷來的錢。它滿是謎團,卻得不出什麼結論,它寫滿了驚奇的一瞥,可笑的觀察,暗湧著新故事。」
我們無法得知沙博爾夫斯基的筆記本長什麼樣子,對於一個記者,一個報導文學家,他的記錄工具必須是一種商業機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把生活裡的觀察都揉搓烘焙成了故事,也許這是因為他所出生的地方:波蘭,以及後來他所對照的地方,土耳其,都提供了一系列與文學親和力極高的屬性:邊緣、夾縫,持續更新。
土耳其是他記者之路的開端,那段日子被他寫成了《安納托利亞的刺客》,「我當時拿到土耳其政府的獎學金,全國只有幾個名額,而我是其中一個。」他先是在伊斯坦堡就學,學土耳其歷史,「那是非常棒的一段日子,我那時還會講一些土耳其語,不過現在都忘光了。」沙博爾夫斯基笑著說。《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原版出版距今 15 年了,多年以來,他常常前往土耳其旅行,有時甚至一年去兩次,對他來說,那裡可以稱之為第二個家。只是後來疫情席捲全球,他才沒有辦法再去。
說是第二個家,或許因為他在那裡看見了波蘭的倒影:「其實我在土耳其時,最大的訝異是發現波蘭人與土耳其人的心態非常相似。我看到這兩個地方都存在著一座『心理的橋樑』。雖然說,波蘭跟丹麥都同屬於基督教國家,理論上應該更接近,但我反而覺得波蘭人與土耳其人更為相似。」
「我後來理解到,也許這跟『邊境國家』的命運有關。波蘭總是夾在東西方之間——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文化之間、歐洲與俄羅斯勢力之間。這種『被分裂』的歷史形塑了我們的心態。土耳其也是如此——永遠在東與西之間擺盪。」他提到了《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全書最初時出現的一位詩人,乘著橫渡歐亞兩洲的渡輪,每天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往返數次。「我覺得那正象徵了我們的狀態——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不斷穿梭。」
此時沙博爾夫斯基見縫插針,進入反擊模式:「我很好奇,台灣的讀者是否也會在這本書中看到某種共鳴?」
𝑴𝒂𝒊𝒏 𝑪𝒐𝒖𝒓𝒔𝒆・與土耳其總統共膳
明明《跳舞的熊》寫的是東歐,但也觸碰了許多台灣讀者對老一輩人深層的疑惑:掙脫枷鎖後反而想念起枷鎖的那一代,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沙博爾夫斯基說:「我想,當一個波蘭人書寫土耳其的時候,台灣人讀來之所以覺得有趣,是因為我們透過了『外國人的眼睛』,去看到一個其實與自己並沒有那麼不同的世界。而香港那種介於英國與中國之間的拉扯,其實與我們在波蘭、在土耳其感受到的『兩個世界的橋樑』非常相似。」
在採訪之前的那個星期,俄羅斯派出了 19 台無人機入侵波蘭領空,純粹只為挑釁。「前陣子,波蘭的市場發生了一場大火,經調查後發現原來也是俄羅斯的滲透行動。他們想要藉著製造混亂讓人民恐懼,這樣就能令社會開始尋求『強人』統治。這正是通往獨裁的捷徑。」這一段話能迴響起《跳舞的熊》序言的聲音:
有著一頭亂髮和癲狂眼神的那人不是憑空出現的。他們之前就認識他了。他有時候會告訴他們,他們有多偉大,並且叫他們回歸到自己的根源;如果有必要,他會穿插一段幾乎不可能發生、但十分吸引人的陰謀論。
「我記得在九〇年代蘇聯解體時,福山曾經講過『歷史的終結』。不會再有戰爭,不會再有衝突,人類將會永遠和平。」這種樂觀雖然天真,但或多或少也讓人臆想一種快樂的生活。沙博爾夫斯基是在獨裁體制底下長大的,在童年和少年時期,國家在他眼底掙脫了枷鎖,進行轉型。「對我來說,那是一段讓人非常興奮的時光,商店從空無一物,變成可以買到來自全世界水果的地方。」
那時候,他們一度相信歷史的終結是真的。
但顯然不是,否則今天早餐的選擇裡,沙博爾夫斯基不會買到來自烏克蘭的火腿三明治。如果人類確實達成了永久和平,來自東亞的我們也未必會對《跳舞的熊》感興趣,作者本人也未必會對我們感興趣。就連土耳其也是如此,「我觀察到這個國家正在改變,而這讓人難過。當看到一個生氣蓬勃的民主制度逐漸被推向某種『輕度獨裁』的版本,是令人心痛的。」
所幸《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寫作期間認識的土耳其朋友依然安好,「我的土耳其朋友們過得還算不錯。基本上,他們都反對政府,也對國家的走向感到不滿。而他們只是努力過自己的生活——這大概是生活在『輕度獨裁』體制下唯一能做的事。」
土耳其是矛盾的,沙博爾夫斯基對土耳其的看待也是。出版這本書後,沙博爾夫斯基經歷了一場魔幻的飯局,他曾與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共膳。
那是由波蘭與土耳其兩國總統共同舉辦的晚宴,而他則是土耳其大使館的座上嘉賓——邀請方不可能不知道, 《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對土耳其的威權統治帶著批判角度,「這份邀請意味著他們了解我的立場,也知道我批評他們,但仍然願意表示尊重與欣賞。而我也因此對這份態度心懷感激。」
據沙博爾夫斯基的回憶,那晚餐桌上出現了鮭魚、鴨肉。兩道菜都是波蘭傳統料理,其中鴨肉更為常見、更廣為人知。波蘭有專門飼養和販售鴨子的地區,而「鴨肉藍莓醬」是波蘭的特色菜。但那晚,艾爾段總統並沒有進食。他面前擺著餐盤,卻沒有上任何一道菜。
當時已經在寫《獨裁者的廚師》的沙博爾夫斯基馬上就理解了發生什麼事:這是一趟當天來回的訪問——艾爾段早上抵達波蘭,晚上就返回。他會帶著自己的食物。「國家元首,尤其是獨裁者,不會在無法完全掌控食物準備與供應流程的地方用餐。換句話說,如果他要吃飯,他必須帶著自己的廚師同行。因此,他在那場晚宴中什麼都沒吃。」
歷史終結之前,人民依然反抗、依然努力過活;而掌權者依然無法對一頓晚餐掉以輕心。
𝑫𝒆𝒔𝒔𝒆𝒓𝒕・讓文學煮
「我們這種像樣的俄國人就是熱愛那些從來解決不了的問題。」契訶夫的人物這樣抱怨道。當 14 歲的沙博爾夫斯基從文豪的警世故事裡獲得想要成為作家的野望時,也許並不知道,所謂的生活就像一棵掛著累累果實的大樹,很多時候沒有任何一顆是能夠採摘的,可能連旁枝末節的零碎瑣事都解決不了。
但或許正是這份徒然,讓 14 歲的他的追望,在假新聞與 AI 生成內容充斥的今日顯得可貴,也讓沙博爾夫斯基在生活與真實之間槓上了一個等號:「我希望『能以文學方式書寫真實』的記者,是最後一批不會被取代的人。」
「AI 也許能寫出偵探小說,但它無法採訪一位廚師。那需要人類的共感與理解。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寫作品質變得更重要。我們必須寫得比 AI 更好,否則這個職業就會消失。」
「我稱這種文字為『非基改文學』(non-GMO literature)——就像歐洲標榜非基因改造的作物一樣,沒有人工干預,純粹自然。」就連文學的比喻也是來自飲食科學,實在是很生活了。而基因改造,其實也算是人類的轉型時刻,它會衝擊多少農民的生計?有多少既定農作方法會被取代?它就像是《跳舞的熊》所關注的對象,就像俄國大地所遍佈的餐桌那樣,就像曾經或正在面臨獨裁統治的廚房那樣,一切都是充滿著生活的故事。
一切都是生活。
伍德對契訶夫的形容之中,還有這麼一段話:「在契訶夫的世界裡,我們的內在生活有其自己的速度,自己弄了一套日曆。而在契訶夫的作品裡,自由的內在生活撞上了外在生活,就像兩套不同計時系統的衝撞,儒略曆撞上了格里曆。這就是契訶夫所說的『生活』。這就是他的革命。」這就像兩個不同大陸的對接,歐洲大陸連上了亞洲大陸。而這就是沙博爾夫斯基所書寫的「生活」。這就是他從安納托利亞帶來的文學刺客。
沙博爾夫斯基接下來會寫什麼呢,進入了受訪狀態的他絲毫沒有半點鬆懈,簡直是守口如瓶。我們只能說一句:讓他煮(Let him cook)。
《安納托利亞的刺客》
《跳舞的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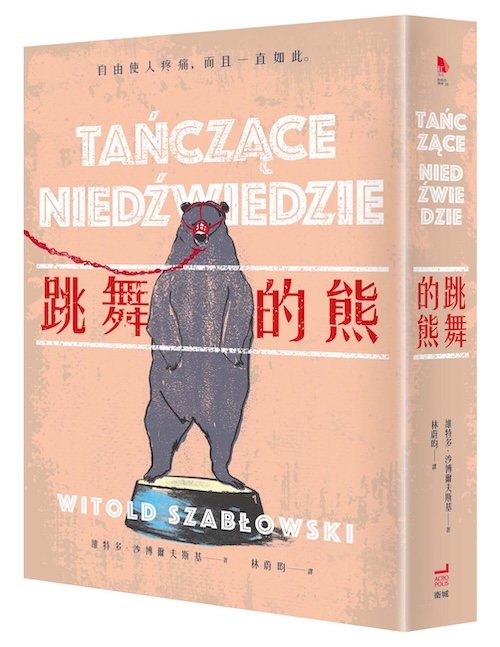
《獨裁者的廚師》
《克林姆林宮的餐桌》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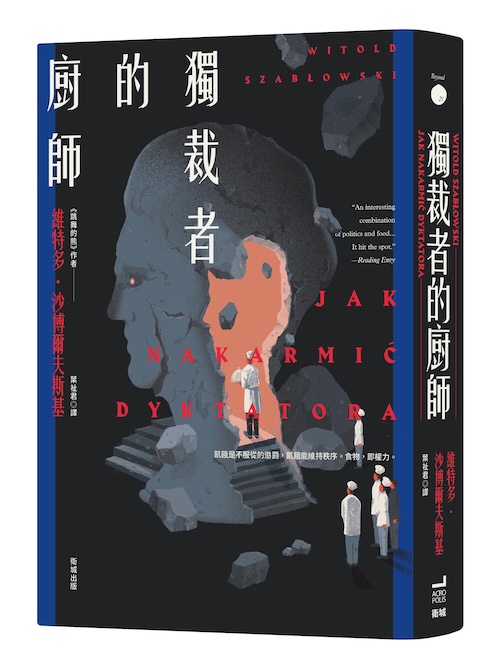
%E5%85%8B%E9%87%8C%E5%A7%86%E6%9E%97%E5%AE%AE%E7%9A%84%E9%A4%90%E6%A1%8C-%E7%AB%8B%E9%AB%94%E6%9B%B8%E5%B0%81300dp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