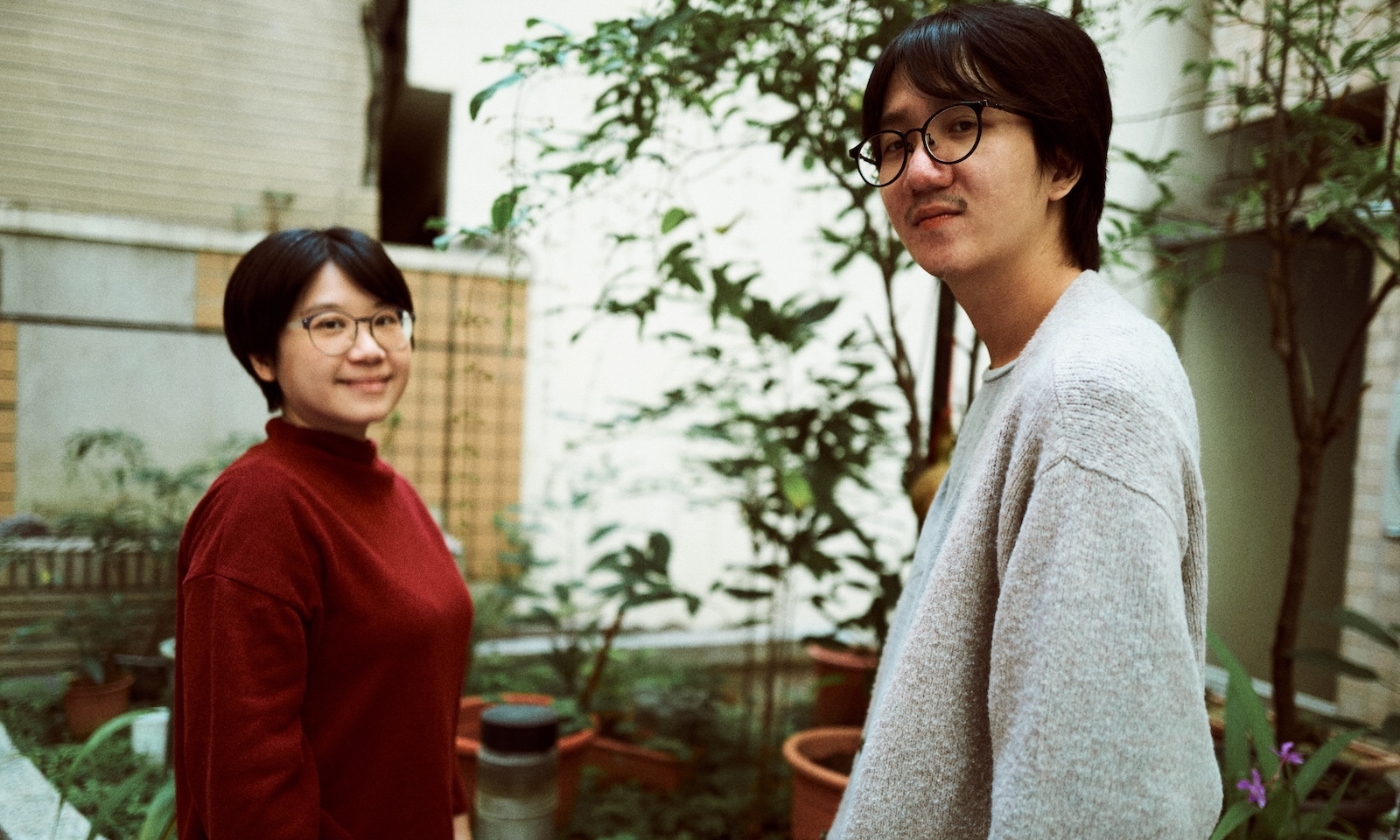
【結婚萬歲,寫作無罪】專訪熊一蘋╳林巧棠:謝謝你接受那個,連我都未必接受的我
告白
熊一蘋第一次讀林巧棠,是在台大台文所的課上。教授帶讀每年的九歌散文選,包括拿下 36 屆時報文學獎首獎的〈錯位〉。知道林巧棠也在台下,教授帶點調侃說,這是名家之作。
林巧棠第一次讀熊一蘋,是耕莘寫作會同儕引薦下,讀了收錄《短篇小說》裡的〈西子灣為什麼叫做西子灣〉,最一開始讀,讀不懂。比起作品,她對人的在意更多一點點。
那天大雨。
台大圖書館不定期舉辦免費的電影放映活動,熊一蘋沒帶傘走進放映室,遇到想回味在金馬影展讓她看到哭的《愛‧慕》的林巧棠。可惜麥可漢內克沒在跟你拍浪漫電影,作品裡癱瘓的老婦安娜逐漸失能,被不忍心的丈夫喬治以枕頭悶殺,熊一蘋看到受不了,走人。
曖昧的開端是,隔天林巧棠問他為什麼提早走,熊一蘋聊起他親戚的故事。
再幾個月後的愚人節,熊一蘋告白了。林巧棠沒有忘記,「我還想說今天愚人節你認真?但看起來好像不是開玩笑欸。」熊一蘋有點慌:「因為我不想把這件事拖過清明連假啊!我就在回老家之前跟她講。」
交往到結婚,寫作的十年有彼此,匯集成兩人的第一本散文。林巧棠形容《臺北是我的夢幻島》是「看到一個小男生純真地面對世界」,熊一蘋形容《不乖乖》是「一個好學生發現自己被坑了」,而小男生與好學生的交集是成長,是霸凌,是學運與啟蒙,是寫作的美與失敗。
是寫作者,也是伴侶。他們是彼此作品的第一讀者,也是人生的。
交往
《臺北是我的夢幻島》與《不乖乖》不只書中內容交集,連兩人的寫作歷程,也出奇地同步。
對不少讀者來說,他們的第一本散文集,太晚出了。
林巧棠以〈錯位〉拿下時報文學獎時 24 歲;熊一蘋更早,19 歲以〈土地神一日〉獲得林榮三文學獎小說佳作,是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以年少之姿登頂大型文學獎,他們沒有順理成章出書成名。不是沒被問過,只是真的沒寫出來。
台文所期間,指導教授蘇碩斌開始有系統地推行非虛構寫作,與兩人約定將論文改寫成書出版,便在他們個人創作前,先有了林巧棠以台灣現代舞為題的《假如我是一隻海燕》,與熊一蘋梳理台灣搖滾樂史的《我們的搖滾樂》、記錄六〇年代美軍如何影響台中的《華美的跫音》。
非虛構力求嚴謹,每天閱讀大量資料,林巧棠還技術性延畢一年好產出作品。但出版後或許是題目太冷門,並未在市場上熱烈迴響——就連入圍了 2020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也不曉得有沒有多賣幾本。
反倒,她更困惑了。「那時候是一個滿大的榮耀沒有錯,但我是不是可能沒有辦法再得到這麼好的待遇了?這本書我花了很多心力,但像散文啊,可能就沒有辦法把格局拉到那麼大、或者是把眼界拉得比較高。」
「得時報文學獎之後,再去投林榮三也都沒有回音。我也會覺得壓力很大:我是不是僥倖才得到時報文學獎的?」
獎項帶來的失落千真萬確,榮譽感卻假得不得了。
文字構築的世界孤獨而華美,喧囂且燦爛,是文學的國度在召喚著我。
而我卻叛逃了。
——林巧棠〈文學救不了病中的我〉
困惑同樣發生在熊一蘋身上,而且更早。編輯數度找上他,「但我把自己的東西看一遍之後,覺得沒有辦法。沒辦法把這些東西集結、出書,然後我會滿意。」
「很多人——尤其是本來對文字的直覺比較好的人——其實很多時候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得到肯定。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寫,大家覺得是好的?我不知道我做對了什麼事情。所以當我沒有辦法複製出一樣的結果,我就會沒有辦法給予自己肯定;或是沒有外部肯定,我就沒有辦法肯定自己。」
於是他一直拖,不肯出書。或至少,不要透過出版社「正式」出書。
那幾年,他以獨立製作的方式發行作品,「我沒有那個自信可以進到出版這個體制裡。大家也說出版不景氣,我就想,那反正我做的也不夠好,那我就自己來做。」包括《超夢》《#雲端發行》《結束一天的方式》都是他當自己的編輯,還有《廖鵬傑》透過 Famiport 列印碼上傳雲端,任全台民眾自行列印裝訂。
列印碼期限只有三天,彷彿流星。未能在文壇激起水花,卻在特定圈子裡成為珍品。但與此同時:
陳柏言出書了,不在讀書會的蕭詒徽出書了,我甚至不知道有在寫的林奕含出書了,身邊開始有人走進那個世界,我幾乎能單純地替他們開心,回頭繼續完成我的論文,交出它,接著開始改寫。那會是我出的第一本書,我慶幸它大致與我無關。
——熊一蘋〈寫作〉
所有人都起飛了只剩他在原地。被屏除在體制外的疏離感依舊,有過間接被否定的經驗,他還是有一點憤慨,「我好歹也是有一個自己做的東西,怎麼好像沒有『正式出版』就不會被業界接受?」
因此非虛構的訓練,某種意義上是在解毒。「以前會覺得說寫東西就是,你一個人靜靜地在桌子前面輸出你的東西,但非虛構會讓你發現,寫作可以不是只是一個靜態的活動,它很多時候是你要行動起來、跟人互動、跟人交流、去找資料⋯⋯」
「寫作可以不只是文學的。寫作可以是很動態的。」包括獨立出版或開始接案寫採訪,那都是寫作的樣子。出不出書、正不正式,說到底不是那麼重要了。
何況還有一種文學,在街頭。
受傷
2014 年 3 月 24 日凌晨,反服貿運動者企圖佔領行政院的那晚,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下令警方清場,鎮暴警察一身黑色烏龜裝,把眾人嚴實包圍,開始驅散,而運動者手無寸鐵——熊一蘋和林巧棠也是一份子。
〈圍城夜奔:三一八手記〉中,林巧棠重新召喚那一晚,包括熊一蘋跟鎮暴警察爭搶「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紙板時,想著,警棍就要砸下來;也寫退出行政院大門後,翻倒的肢體佔滿視線,有人的腿已經彎曲殘廢,有人流血;還有水車,最恐怖的水車撲面而來。
人們正在受苦,國家暴力打在身上。
我和一起逃出來的幾個人,都沒有流血。甚至沒有被噴溼。於倉皇的夜色裡逃離,我心中必須想像自己被水車裡惡臭難當的水全身噴個透徹,彷彿只有這樣才足以彌補內心的罪惡感,才能感覺自己並不那麼狡猾。
——林巧棠〈圍城夜奔:三一八手記〉
體膚無損,但內傷是即刻的。剛出行政院熊一蘋放聲痛哭,「人在你面前被拖、被打,我覺得衝擊是滿大的。我也有寫到現場的警察,他們沒有辦法把人當成人看,就是我覺得人對另外一個人基本的——」
「尊重嗎?」
「不是。就只是『不要傷害他人』,或是『有人在你面前感到痛苦的時候,要盡量去幫忙』⋯⋯這對我來說原本是很基本的,但那個現場完全不是。他們就只是急著要把所有人弄出來,不管你卡在牆角很痛幹嘛,他們就只是在實行一個命令,人跟人之間最基本的互信都已經消失——這件事情給我很大很大的衝擊。」
後來,熊一蘋寫下〈對與錯與我們的超展開〉,因為他知道,如果不寫,會傷得更深。「你不寫創傷,才會變成一個創傷。我 324 回來,我把同一件事情跟我室友講一遍、又跟其他朋友講一遍,然後又寫了一遍,因為那個東西不把它用語言重新組織,它會一直留在我的心裡。」
反而距離事件到提筆,林巧棠等了十年,因為「怕中國統治台灣啊!」
朋友的父親曾到中國探親時被帶走,筆桿上壓著恐懼的重量,杞人憂天卻也務實。直到去年《報導者》與《鏡週刊》紛紛推出回顧學運十年的專題,重看照片,林巧棠下定決心。
我害怕,連字眼都害怕。破門而入,警察,黑夜,街道,占領,盾牌⋯⋯就連那些日常的詞彙都能挑起我敏感的神經。噴水,水車,人群,手勾手,行道樹,人行道,黑色。
——林巧棠〈圍城夜奔:三一八手記〉
拾回碎片,才發現不全是痛苦。比如民眾被驅離時仍有一股力量透過手臂撐住大家;比如行政院外為他們鼓掌的人;比如後來,熊一蘋所屬的輕痰讀書會在街頭上發起了《街頭副刊》。
讀書會向關心運動的寫作者徵稿,當時熊一蘋甚至不會用 InDesign,還是林巧棠教他的。一行人拿去立法院旁的影印店印刷(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影印店老闆沒有收錢),在善導寺捷運站旁的麥當勞旁邊折好,上街頭派報,有人呼喊:「有人需要文學嗎?」
有人接了過去。一個、兩個、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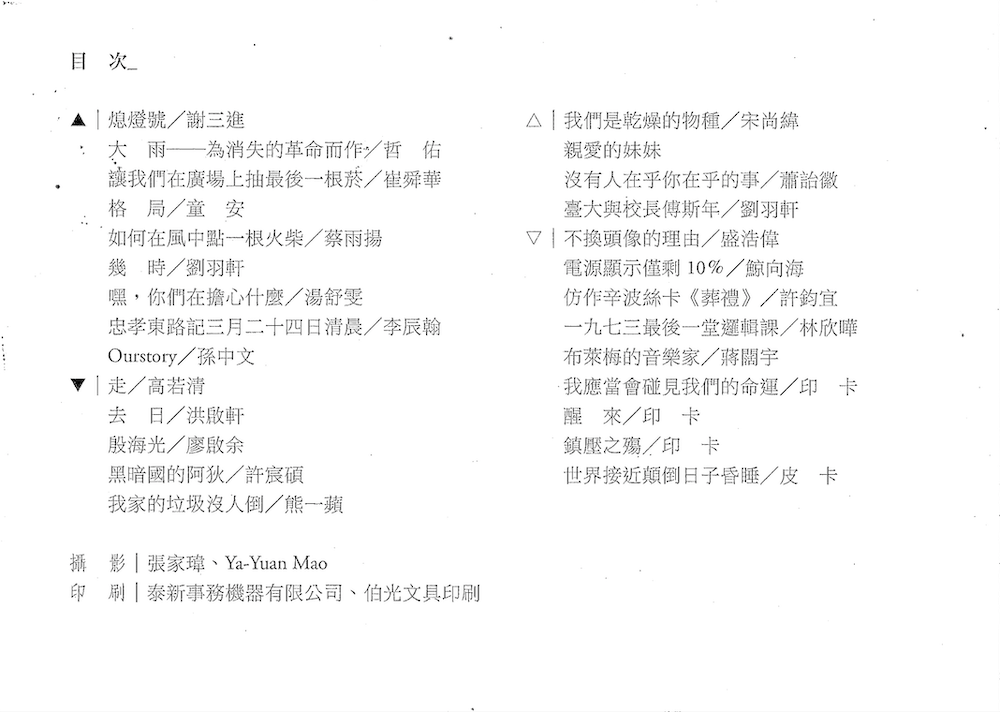
目次一字排開,有些作者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去了哪,但更多的是如今依然以編輯、以創作者身份活躍的名字。
《街頭副刊》很快就發完,對熊一蘋來說這是一件「再不做就要崩潰了」的事;但在林巧棠眼中,很美:「平常這個社會對於文學很冷漠、或者是說這個社會根本就不關心文學、輕視文組,但在經歷這麼大的事件之後,好像人們心裡有一些空缺是其他事情沒有辦法填滿的。」
她寫:那正是文學之神「在場」的時刻。
我最怕的,就是到頭來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和一起從圍城裡逃出來的人們,把這則故事講給許許多多的人聽,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這成為所有人的故事為止。
——林巧棠〈圍城夜奔:三一八手記〉
同居
如果 2015 年 Uber Eats 就已經進入台灣,兩人恐怕不會同居。
碩二那年林巧棠生了一場大病,嚴重的腸胃炎讓她無法下床,但宿舍是單人房,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她買東西,只好打給熊一蘋。沒人照顧實在撐不下去,剛好熊一蘋住處租約也到期,「我就想,那如果住在一起的話,有一個人可以照顧我。」
他們搬去永和一間 6 坪大的住處。
在那之前,林巧棠少有與家人以外的人同住的經驗;熊一蘋則是太多了。上政大那一年,與中文系五人一起住在 15 坪房間,他跟另一位室友在和室桌子兩側打地鋪(還有辦法一邊用電腦),就這樣住上一年。後來也住過萬芳醫院附近的頂加,房間是L型,巧拼加毯子湊成床。
能捱過這樣的波折,歸功於熊一蘋的高容忍度;反之,林巧棠敏感於各種細小變化。同居時,兩端差異開始作用,反覆磨合成為基調。
剛搬到永和時,棠每晚都哭。每件東西都不合適,房間太小、床墊硬、櫃子太少,她必須把愛書收在床底下。問題大多無法解決,我每晚哄她,幾乎精神衰弱。
有天我照常安慰她,問怎麼啦?棠抽泣說,這裡不是她的房間。
——熊一蘋〈少年經事〉
身體的差異,是健康的,更是性別的。
彼時輔大心理系性侵案、母豬教、同志遊行等事件層出,林巧棠在種種仇女言論帶來的情緒波動裡,一次次疼痛、虛弱;而儘管是陰柔異男,熊一蘋知道自己仍無法完全同理對方,這是他的女性主義第一堂課。敗北與妥協之間,他們彼此折磨。
林巧棠在那時決定好好調養身體,「必須這樣做不可。我唸書唸一下子就會開始頭暈。就覺得不休息不行。」儘管這意味著部份收入面臨真空,在同輩人衝事業的時期停滯,需要賺錢的念頭也阻撓了寫作,但他們不後悔。
「巧棠她選擇把心力投注在自己的健康上,很認真把過去累積的這些傷病都養好,我也有在一起生活的時候看到她確實越來越好——在大家都投資其他東西的時候,她願意投資健康,是我覺得很了不起的事情。」熊一蘋說。

那年夏天過去,兩人生活漸漸好轉,只是性別的荊棘沒有輕易放過熊一蘋。
包括〈少年經事〉在內,《臺北是我的夢幻島》裡有三篇散文被他合稱「性別三部曲」。〈晾她的衣服〉寫他小心翼翼為她晾衣,各種鋩角(mê-kak):圍巾要攤平著晾、內搭褲不能用太大的衣架、細肩帶的衣服要用有凹槽的;同時也寫對買衣服的恐懼,走進 UNIQLO 會恐慌發作——對這樣一個異男來說,想變好看的慾望是醜的。
〈可是亂馬就可以〉寫性癖。他對澆了冷水就變成女生的亂馬抱有性慾,也包括《航海王》裡的荷爾蒙果實,《銀魂》裡的集體性轉,《哆啦A夢》裡變成靜香的大雄,甚至是《短路西遊記》裡喝了女兒國泉水便能懷孕的唐僧八戒⋯⋯性轉使他興奮,他更加懷疑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性?
寫下〈可是亂馬就可以〉第一個版本,朋友評價溫暖,但「我很希望大家用更 critical 的角度點出,這一篇發表後可能會起怎麼樣的爭議⋯⋯後來也沒有這些事情。」修訂成如今的版本,少了故作鎮定的剖白,更多是承認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看待自己。


全文在副刊刊出後,粉專下的回應也都是「細膩」「完全懂完全懂」,他唯一回覆的留言,是請他投稿給黃麗群的 Video Podcast 節目「還是你想被罵」,他回:別。
假想的批判沒有發生,「我心裡面有一個落差,不能接受。但我後來才發現說,其實是我在歧視我自己。我認為這件事情是需要受到譴責的。這是一個內在的歧視——我透過譴責我自己,來跟自己達成平衡。」
林巧棠也還記得他忐忑坦承性癖的那天,「他非常認真、非常慎重——告白都沒那麼慎重——我想說,不行我一定要好好回答。」後來她給了個嗯,尊重多元性癖。

但既然難以啟齒,為何不寫成小說?熊一蘋說這不是虛構的責任,「我不想要躲在一個外殼下。我覺得這一本書是,我因為寫東西認識的人對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今天要正式投入文學社群、要先自我介紹的感覺。」
「我要讓大家認識我,不能只認識平安的我,要認識就要認識最深沉的、連我自己都未必能夠接受的那個我。」就像——「在交往前先跟對方講我有一大堆缺點的那種感覺吧。」
林巧棠說他真的有這麼做。
結婚
婚後他們搬到台南,由於是親戚的房子,能以少少的租金換到大大的生活。
不台北、也幸好不台北的生活。
林巧棠說,「我從大一開始就住在台北,住了十三、十四年吧,生活步調很快,而且消費其實也越來越高。」儘管需要犧牲藝文活動、硬體資源,但這裡天氣好,他們各自有書房,好吃的飯與可以好好吃飯的餐桌,他們戲稱現在像退休。
「會發現,在台北的時候,我們真的把自己搞得好累!」熊一蘋吶喊。
書也是在來台南的這一年出版的,生活騰出來的空隙,讓他們能重新面對逃離過、拖延過的寫作。
2023 年有一陣子林巧棠生病、回家休養,獨處的時間裡慢慢把以前的東西集結,也開始寫起被霸凌的經歷,忽然就是一本書的量體。熊一蘋則是因為搬到台南,自由工作的案源與型態隨之轉移,「想要拿補助的錢。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子啦。」
走進那個世界了,出書如今不再承擔過載的意義。就是帶一點私心的工作,活下去之必要。
所謂私心是,「書出來之前,我都覺得一定超級好看!結果書真的出了之後,我就覺得糟了糟了,會不會大家其實覺得這個東西沒有很重要?那個自信瞬間就不見了。」熊一蘋說。
「我的事情大家真的在乎嗎?」目前收到的讀者回饋,還沒多到消除這份不安,但相比過去的心態,他自覺已經健康許多。畢竟最一開始,寫作是為了報復,「會有一個幼稚的想像是,我把這些事情寫出來,大家覺得好棒、會說『你那個時候辛苦了』⋯⋯」
「但也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像。我覺得很多人是抱著這樣子的想法去寫作的,但這樣太辛苦了、其實是對自己的傷害很大。」他們在找的,是寫一輩子的方法。

宋欣穎導演曾告訴熊一蘋:「你是那種會寫一輩子的人」;林巧棠在散文裡承諾自己:「這條路我要用一輩子去走」——好大的一輩子,但也因為是這樣好大的一輩子,「所以才會去煩惱文學啊。」林巧棠說。
文學賺不了錢,文學買不了台北的房子,文學給不了財富自由。林巧棠也幻想過,如果當年在竹女畢業後當上竹科太太,可能現在煩惱的是要買哪一顆包包,「我其實有點心動,但我看過有些女性在那樣的生活裡其實是孤立無援的,必須要組成一個自己互助的團體,因為她們沒有工作的,生活就只剩下小孩跟『我可以在超市買到什麼特價的東西』。」
不是要貶斥那樣的生活,只是那並非她想要的。反正就像〈少年經事〉寫的「到處都是時代」,不如選自己喜歡的。
熊一蘋也問過自己,如果大學不是讀中文系呢?會有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吧?有一個大家想要的生活吧?可是他回不去了。前陣子跟父親起爭執,發現有些情緒懸在父親嘴邊、卻無法凝結成語言,「他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痛苦、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痛苦這件事,在我看來,比當事人所能夠意識到的更加難受。」

如果沒有文學,就不會在行政院門口哭;如果沒有文學,能住上比 6 坪大得多的房子;但「如果沒有文學,我可能會帶著很多我無法理解的困惑,一直、一直生活下去。」
能夠言說就是一種特權。文學不是什麼都沒有。
林巧棠想起李鴻瓊老師對她說:你要從文學的美學,走到文學的存有,再走到文學的道。「『存有』是一種存在的狀態,不是停留在單純的美感經驗,而是深入到人的生命裡面去描寫。」
至於道,是那樣的一輩子。
熊一蘋說,「並不是要一輩子當一個作家,而是一輩子持續寫作。」
這樣的一輩子。
《臺北是我的夢幻島》
-%E7%AB%8B%E9%AB%94%E6%9B%B8%E5%B0%81-300dpi.jpg)
《不乖乖》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