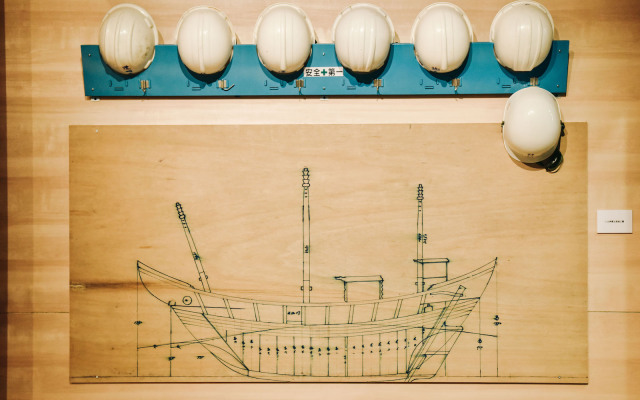黑白嬉遊,大話黑 sell ——專訪《黑紙》雜誌
剛到香港的那幾天,我重新適應著這裡的時間和距離,紅綠燈的秒數、地鐵的速度、一條街的長度。走進 7-11,少了御飯糰和那排讓人有選擇困難症的飲料架,但多了一整櫃的喉糖、口香糖,以及《黑紙》。
當說到香港的雜誌,很多人都會直接想到八卦或時尚雜誌,充斥著富麗堂皇的圖片以及斗大聳動的標題。《黑紙》的出現幾乎是在反其道而行,首先它的量詞不是「本」,而是「張」,一張寫滿了黑字的紙,沒有圖(除了封面一張名人黑白大頭照),沒有八卦,只有流水帳般的短句,且字字珠璣。林日曦、陳強和阿 Bu 三個人的創意,製造出一張張道地港式風味的文句,在俗稱「文化沙漠」的城市激盪出不甘平凡的綠洲。
2011 年 12 月《黑紙》拋出一句:「鉛筆像人生,總有完畢的一天」,然後闊別了兩個月,正當我以為從此和《黑紙》無緣的時候,它又以「偽廣告雜誌」之名重出江湖,甚至從一塊錢港幣變成每個禮拜免費派發(撐了十期免費後撐不下去,後來還是變回一元一張)。這次到香港,第一個任務就是直奔《黑紙》工作室,與三位創辦人兼寫手會面,聽聽《黑紙》黑 sell 的黑色信念。(「黑 sell」用廣東話唸起來音似「Hard sell」)
Q:是怎麼樣的機緣下會出版《黑紙》?又,出版《黑紙》的目的是什麼?
陳強(簡稱為陳):我們三個人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同一家商業電台,彼此在那裡認識,一起成長,並且成為朋友。那時候就想要一起做些事情,廣東話俗稱為「搞D野」,想想不如就辦份雜誌吧。所以是先有雜誌,之後才有創作公司。其實《黑紙》的初衷比較像是在聯誼,想讓大家開心、放鬆,沒想到發現有一群數量不小的人支持我們,慢慢覺得這份雜誌可以維持下去,於是過了一年多,也就是 2011 年的年中,《黑紙》從單純的一張雜誌正式成立為一間公司,開始認真地去營運。我和林日曦也退出電台,完全投入「黑紙」工作,自己付自己薪水。
當然,一路發展下來會知道,若僅靠出版《黑紙》根本不足以生存。當「黑紙」變成創作公司後,我們發現除了做雜誌外,還可以做廣告,與客戶互相幫助,客戶需要曝光,我們也可以從中賺取生活費。另一方面,除了紙張的形式,我們甚至可以拍廣告、策劃一場 show 或一場活動。這讓我們有能力可以持續發薪水和聘請新的同事。
到現在這一刻做了大約三年,我們也很難分析這件事情究竟是好還是壞,是不是一定要靠這些商業行為才能夠生存?這樣是不是健康的呢?香港可不可以只做文化就能生存?類似的問題我們至今還沒找到答案,依舊還在摸索之中。我們唯一清楚的,是現在的狀況如果單靠《黑紙》根本無法存活。
林日曦(簡稱為林):《黑紙》的誕生是在 2009 年尾,當時我們三個各自都有工作,同時想著「搞D野」,但究竟要做甚麼呢?很多年輕人,無論是香港或是台灣,總會有想做事情的衝動,尤其上班之後會感覺生活很枯燥無聊,常會想要做點「什麼」。我們思索了一段時間,為了不影響當時的正職,這個「什麼」不能太沉重,工作壓力不能太大,最好是個可以出版的東西,那不如就出一張紙吧。那紙張裡要有什麼呢?我們就打算用文字填滿整張紙,成為一張寫滿字的紙,且都是短短的句子。
其實這整件事情很「僆仔」(毛頭小子),就是像 facebook、微博那樣把每件事情都寫得很簡短。我們三個人寫東西的習慣向來如此,我們也相信現今的讀者,在現在這個年代如果拿到一大本雜誌根本不會想仔細翻閱,就算是翻,大部分都是沒有意義地隨手在翻,倒不如我們直接出一張寫滿短句的紙。
Q:為何取名為「黑紙」?這與林日曦的專欄〈白紙〉有關係嗎?
林:有了出版的概念後開始思考名字,當年輕人在「白紙一張」上把自己的想法寫盡、寫滿,寫到沒有任何空位可以在寫,自然而然便會成為一張「黑紙」。大家認識我主要是因為《黑紙》,導致後來當自己有了一個報紙專欄,也要取名字時,我就用了「白紙」。但〈白紙〉主要是寫一些我個人對於社會的看法。
Q:從一開始的「偽文學雜誌」、「偽娛樂雜誌」,到現在的「偽廣告雜誌」,這當中的內容有什麼改變?又有什麼是堅持不變的?
陳:三個主題是三個不同的年代,第一年「偽文學雜誌」的想法來自於我們對「寫東西」的迷思:是不是寫下來的東西就叫做文學?文學的文字是不是一定要讓人覺得艱澀、苦澀?我們做「偽文學雜誌」在某程度而言是在嘗試衝擊大家對於文學的思維。我們並不認為自己寫的是「那種」很艱澀的文學,但難道「這種」就不能被稱作文學嗎?
而第二年機緣巧合下《黑紙》在 7-11 上架,既然要面對更多的群眾,我們就在 2011 年 1 月開始,用每一期訪問一個明星的形式來做。而一旦開始要訪問明星,這本雜誌就等於和「娛樂」扣上了關係,但是不是娛樂雜誌就一定要寫八卦、狗仔跟蹤等消息?難道娛樂圈的藝人沒有思維嗎?於是「偽娛樂雜誌」便有了衝擊傳統娛樂雜誌的目的。
經過一年,能衝擊的也差不多了,今年,我們轉變方向去思考廣告:廣告是不是只能用來推銷?什麼才是適合現代的廣告?於是形成了如今的「偽廣告雜誌」。這個概念稍微複雜一點,我們想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推銷自己,如何營造整個 layout,這並不是要直接衝擊任何一本名為「廣告雜誌」的刊物,儘管香港確實有「廣告雜誌」這類的名堂,但我們想表達的,是人們並不需要透過電視廣告之類的行為去認識一樣東西,重點是你怎麼去營造自己。今年我們希望能衝擊大家對於流行文化的思維。
.jpg)
Q:《黑紙》每期都會以一個主題來訪問一位明星,這些主題是如何構思出來的?
林:頭兩年的 Topic 主要是我們自己定,每月每期出版之前大家開會,三個人互相丟 idea 出來,內容都是我們所希望表達的東西。今年則有點不同,「偽廣告雜誌」的想法是:sell 的東西不一定是件商品,於是有了「黑 sell 黑色信念」的概念,我們賣廣告的同時可以把信念也賣出去。在這個前題之下,我們雖然依舊在訪問名人,但題目由對方來開,希望讓名人自由發揮,透過故事或經歷來告訴大家他所相信的「黑色信念」。所謂「黑色信念」,就是一些負面的、改變不了的缺點,而既然改不了,不如反過來相信它吧,將它融入自己的人生,反而對自己以及這個世界都有好處。
等名人開了題,我們才開始按照那兩個字的題目來創造我們三個的「黑句」。上一年也有很多名人訪問,但那時候的題目是由我們想出來,且往往跟時事扣上關係,或例如說找到吳彥祖,發覺他的背景是在外國生活的香港人,那想必他小時候在國外有被歧視的經驗,於是我們就想聽他聊聊歧視問題。有趣的是,儘管這個的題目是我們訂的,但在訪談之中吳彥祖主動點出了「中國人歧視中國人」的概念,因而引發出另一個主題。
Q:要在香港雜誌界生存並不容易,《黑紙》是如何辦到的?
阿 Bu(簡稱為 Bu):香港潮流轉得很快,我們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比潮流轉得更快。潮流就是不重複,而我們三個都很怕重複的事物,所以你會看到《黑紙》每年都有轉變。當我們發覺寫的東西逐漸顯得老套,就會想要轉個形式和玩法,讓這個雜誌能不斷給予人們新的感受。
Q:「黑句」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林:好比說要七十句「黑句」,三個人各自回家寫五十句出來,然後開會、互相批鬥、打架,不斷在那一百五十句的草稿裡循環,逐句討論哪句要哪句不要,這樣的過程我們持續了三年。
陳:例如陳豪那一期的「傻勁」,大約兩三個月前就已經做好訪問,而信念這回事又不像一般資訊那樣有時效性,他的黑色信念是不會改變的,因此訪問完之後我們可以慢慢跟著主題寫我們的「黑句」,不用趕。
Q:目前為止,哪一期的訪談讓你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Bu:有幾個都蠻深的。第一個大家都會選謝安琪,因為那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訪問,那一期討論的是香港的八卦雜誌,說這些雜誌不斷揭露別人的隱私、做很多狗仔的事情,令很多藝人都不舒服,而八卦雜誌總有藉口說「讀者喜歡看」所以他們會繼續這樣做。謝安琪於是用了一個比喻來表達做傳媒的應該要有良心,要有自己的道德責任,她說:「孩子喜歡吃屎,你就給他餵屎?」
重點是這一期出刊後的故事,當時《東方日報》刊說網友對謝安琪的「餵仔(小孩)吃屎論」表示不滿,但這一篇報導剛好就反映了《東方日報》正在「餵仔吃屎」,因為事實上全部網民都在按讚,《東方日報》卻偏要扭曲說網民反對。這個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一個傳統媒體的《東方日報》竟然印證了謝安琪在我們《黑紙》裡說的話。
至於今年的話,我們都覺得張敬軒的「抑鬱」不錯。原因……這樣說吧,他的訪問是最難寫的,因為太多東西可以選了,他說得太好,我們卻只有半張紙的空間可以把他的話寫進去,雖然訪問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鐘,但幾乎每一句都是金句,例如「決定我們命運的不應該是性格,而是智慧」等。再者,他用一個廣州人的身分去看香港這個社會,竟然比其他香港藝人看香港來得更加透徹,像說香港的住屋問題令他的抑鬱加深,覺得政府應該解決住屋問題云云,這些都正中香港現時的問題,因此印象也非常深刻。
Q:Youtube 和《黑紙》都只摘錄了極小段的訪問內容,像您方才提及張敬軒的採訪過程句句精彩,未來會打算把那些遺珠集合刊出嗎?
林:不會。這也並不可惜,因為多就淡了。我們已經把最經典的選出來,十句經典的就夠了,就算另外有十句看起來也不錯,但把它們加進去,味道就沖淡了。好比說「黑句」,我們其實可以寫出一千句,或是每一句寫長一點,但那樣就變淡了啊。一定要取捨,要正中、要短,要控制在一定的時間和範圍之內。
Bu:這個做法紮根在我們三個的心裡,可能跟我們一起創作的成長有關。大家都是做商台的,像我和陳強做音樂節目的時候,短短五秒內就要用一句話表達重點,而林日曦是填詞的,每一段曲子都有字數限制,每個字都必須是重點。這個特質來自我們以往所訓練、所學習的東西,我們也都相信這套價值是對的。
陳:套用在今年「偽廣告雜誌」裡也很合適,廣告就是如何用最短的東西來發揮最強的力量。這個精神是重要的,在現在這個世代,無論微博、Facebook 都像廣告一樣,我這裡說的「廣告」並不規限於商品,而是那個氛圍、味道、精神,現在這個時代就是喜歡如此這般。因此「黑句」、Youtube 都不可以長。
Q:《黑紙》出版之後,是否有帶動年輕一輩的創作風氣?或,有否其他刊物仿傚《黑紙》的作風?
Bu:有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天我在電台做了一個訪問,內容是現在網路上一部著名的小說叫《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我訪問了這位作者,很厲害,我可以大膽的說,他是「香港九把刀」。
我先跟你們分析一下這部小說,它是網路上的懸疑小說,非常好看。在香港高登論壇裡,有兩個傢伙出了名寫故事,一個是向西村上春樹《一路向西》,另一個是小姓奴,都是「講故台」的榜首,但他們講的都是「鹹野」(色情文學)。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的作者 Pizza 完全不講任何色情內容,卻也同樣受到熱烈支持,是高登論壇裡首位不寫色情內容而如此受歡迎的作家。
至於他跟《黑紙》有什麼關係,其實是因為那天我訪問他,他跟我說他一直有在看《黑紙》,且受到《黑紙》啟發做了一個 project:聯合了十多個朋友,每個月都要寫一篇小說,然後在網路上建構出一個城市。而出發點就跟《黑紙》一樣,覺得香港這座城市太過於單一化。他們的做法是十幾個人,每個月訂一個主題後,無須討論溝通,各自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城市,例如第一個月主題是「吃飯」,大家就各自寫這個城市應該吃什麼,有的是巧克力,有的是 pizza,然後建構出一個多元化的城市。他跟我說這是取材自《黑紙》,雖然兩個月後這個計畫就收攤了(笑)。
此外,有時候我們辦活動,像讀者聚會、簽名會之類的,我們都會收到很多「偽黑紙」,有白紙、灰紙、黃紙、綠紙,什麼紙都有,每一張都是用「紙」的形式來寫他們自創的「黑句」。我覺得不用管這是不是在抄襲,最重要的是這是創作的開始,而我希望他們最後能創出屬於他們的東西,無論是一個計畫還是一篇文章,當中的精神都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不再只是在做「偽黑紙」。
.jpg)
想認識更多的《黑紙》請參考:
網站:http://www.blackpaper.com.hk/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blackpaperclub
頻道:http://www.youtube.com/user/BlackpaperHK
以及……香港的便利商店。
延伸閱讀:《黑紙》雜誌,引領香港社會的「黑句」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