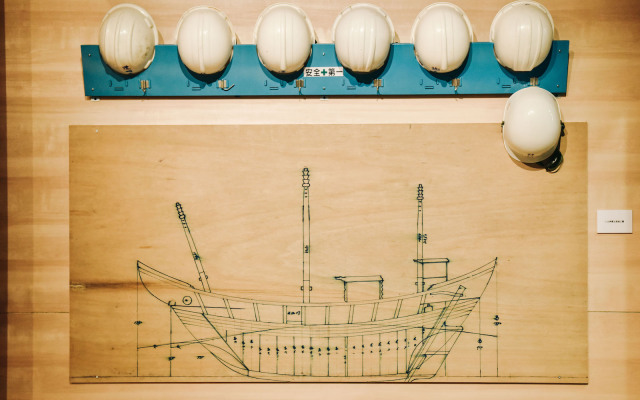許多偶然,回頭看都是必然──專訪《偶然是個魔法師》藍漢傑
「你常常旅行嗎?有沒有覺得,在旅途中對『偶然』的體會特別深刻?」
午後,與藍漢傑相約在台北東區的咖啡店,甫提出第一個問題,他便慧黠地將問號丟回。確實,在熟悉規律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慣於一成不變,巧合的魔法從來不起作用;奇妙的是,當離開了舒適圈,我們往往能敞開胸懷與人相交,間接加強了緣分來臨的力道。在旅途中,人們從來逃不過「偶然」的操縱,而於行路中相遇者雖眾,但這些萍水相逢的人,卻鮮少成為彼此生命中的固定班底。
「旅行在心中留下的不是風景,是人。他們可能只匆匆跟你喝過一杯咖啡、聊聊天,但在你心中會留有一定的位子。未來某一天,你恰巧碰觸了記憶的門,他們又會在你的腦海中出現。」
如果真的有所謂「記憶的門」,那麼《偶然是個魔法師》這本書便是鑰匙,除了能讓人在書中的城市漫遊,更能深潛入回憶的大海,與生命中曾出現的「偶然」,再度相遇。
.jpg)
用文字,捕捉旅外的浮光掠影
《偶然是個魔法師》是藍漢傑的第一本書。正如書腰所述,這本「洋溢旅行感的小說」,靈感確實來自作者長年旅居國外的記憶。十幾年的歐洲時光中,與數不清的人相遇、相知,藍漢傑以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慾望街車》主角布蘭奇的經典台詞:「我都是依賴陌生人的慈悲」來形容旅途中陌生人給予的溫暖。「在旅行中,真的得到很多陌生人的幫助,可以當作是偶然,也可以說出外靠朋友吧!」藍漢傑有些感傷地說,從負笈出國留學、在機場與爸媽說再見的那一刻開始,他便不斷地學習如何與人告別。三個小時的火車旅途中,你可能與萍水相逢者相談甚歡,但走下列車後,卻沒有強大的動機繼續聯絡──這三個小時無疑是深刻的,但相較於與親友共度的時光,卻只不過是浮光掠影。

越是細膩的情感,在心中埋得越是深厚,回憶及歲月的雙重積累,終使藍漢傑化感觸為文字,提筆刻畫記憶中短暫而深刻的片段。從小便喜歡寫東西,出社會後亦以翻譯、記者等文字工作為業,恩師汪其楣看出藍漢傑的才華,不斷勸誘他書寫,但他卻一直沒有真正進行創作。直到 2011 年底,藍漢傑在柏林用早餐時,一位德國女人上前搭話,他請一位路過的年輕人幫忙翻譯。
「在年輕人離去後,我突然覺得,這個人是有故事的,但並沒有馬上開始寫。第二天,當我穿過一座公園、走到一間我很喜歡的咖啡店時,腦中突然出現音樂,我試著描述那音樂,接著開始寫,一發不可收拾。我像是靈媒一樣,聽過去的人不斷在夢裡辯論、和我說話,一個個故事就這麼出現。當時我每天一起床就開始寫,把過去的記憶全化為文字。」
藍漢傑用一年的時間,將自身及友人的經歷寫入《偶然是個魔法師》。比起架構嚴謹、主題明確的「小說」,藍漢傑認為法國文學分類中說書性強烈的「敘事」文體,更適合用來形容這本書。書中十二個篇章以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為背景,分述十二個人物的際遇,他們看似獨立,卻在彼此生命中互相穿插、影響。
在當代文學及電影中,類似的手法並不少見,令人驚訝的是,影響藍漢傑採取這種創作方式的,竟是武俠大師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小龍女的故事雖然在《神雕俠侶》中完結,但當楊姓黃衫少女於《倚天屠龍記》中登場,意猶未盡的書迷馬上可在她身上找到小龍女的身影,回想起上一代的淵源。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藍白紅三部曲》系列作也有相似的特色,三位主角在彼此的人生中一閃而過、無足輕重,但在自己的故事中,卻是唯一主角。

為了貼切地捕捉浮光掠影之感、強調片段與片段間的關係,藍漢傑在書寫時刻意將「主角」的存在感剔除,讓十二個同等重要的角色,輪流登上舞台。「我並不是從整個結構、主題為中心來思考如何表現,而是以人為出發點,先建立十二個角色的個性,再建立關連。」在藍漢傑眼中,這便是呈現人生縮影的最佳方式──廣大的世界中,毫無關係的人們,因「偶然」的魔法而巧妙連結。
被戳破的肥皂泡泡會馬上消失,但生命中的小片段就算離開了視線,仍會靜靜躺在記憶底層,不受歲月摧殘。每一個感官知覺,都可能喚醒人的記憶、將人與過去的殘影相連;年輕時相遇的面孔,也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後的某天偶然重逢,藍漢傑和《偶然是個魔法師》美術設計陳文德的緣分,便是如此出人意料。「我陳文德十幾年前就認識了,當年相遇時,絕對想不到有一天我會寫書、由他擔任設計。沒有人有那麼大的創意和想像力,能在當年幫你預測未來,唯有走到此刻,你才會知道故事全貌,我想這就是生命美妙的一面。每個人都要堅強地活下去,為了知道命運的伏筆。」

暴力與和解
在《偶然是個魔法師》多個章節中,「安妮的日記」像是串場的信物般不斷出現。以日記紀錄生活,亦是藍漢傑長年的習慣。初到法國留學時法文程度不佳,因此只能在心中以中文和自己對話、不斷地寫──不思考文體及結構,單純讓筆、手和意識自由溝通。在巴黎,藍漢傑利用寫作自我療癒、沈澱心靈,同時也大量閱讀他人出版的日記,《安妮的日記》也是其中之一。
「在台灣第一次讀《安妮的日記》時,對暴力、人類衝突的感受沒有很深。到了歐洲我重讀了一次,有了不同感觸。」《安妮的日記》由猶太女孩安妮.法蘭克書寫,描述納粹佔領荷蘭時躲藏於阿姆斯特丹密室的日子,二戰艱困環境下人們的不由自主,在十三歲女孩筆下忠實再現。「它對歐洲青少年深遠的影響,早已超越單純猶太紀實的地位。在歐洲,我處處可見對戰爭、暴力的反省,回頭看台灣,卻是無法面對歷史。原因可能是缺乏自信,也可能是民族性的影響──我們很難把醜的事情講出來。」
雖長年旅居歐洲,藍漢傑仍不斷從遠方關注著台灣的動靜,他藉由創作抒發對故土的關懷,也試圖傳達「和解」的理念。在《偶然是個魔法師》中,除了《安妮的日記》外, 書中提及的文學作品、音樂,都和暴力、戰爭的主題有所關連;書中十二個人物,亦有「化解衝突」的共同特質。心思細膩的藍漢傑,甚至以兩位人物眼珠的顏色,作為台灣藍綠兩黨的象徵。
「對於台灣過去的不安定、藍綠的對決與內耗,我試圖透過感性的方式來陳述,期待能化解對立。但我並沒有想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也沒有想真正去改變什麼,只希望能用善意的方式去影響周遭的人,帶出平和。」面對紛擾的大環境,低調、重感情的的藍漢傑,選擇用一個個隱喻,靜靜地將對台灣深切的情感藏在字裡行間。

感受多於思考,才能真正了解自己
《偶然是個魔法師》是要獻給「在臉書輝煌時代前相遇的人」,社群網站的發達,到底在人們身上造成什麼轉變?藍漢傑認為,語言溝通或許是上天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但當人和人的溝通過於頻繁,周遭的雜音會讓人難以找到自己。「臉書發達後,我們總是想著要怎麼樣陳述自己,多過於去發現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書中〈嘉文〉一章,描述的便是一個找不到自我的台灣女孩,在進入社會前的抉擇故事:捨棄申請美國留學來到巴黎,卻轉念決定旅行,最後出乎意料地在德國完成學業。面對未來,「找不到答案」是每個人都曾面臨的問題,對於年輕人身上常見的隨波逐流、喪失自我,藍漢傑認為除了教育模式是重要關鍵之外,台灣缺乏自信的大環境也有深厚影響。
「嘉文的徬徨,我也有過。大學時,有一次我坐在火車上,在旅程中不斷問自己問題:我想要的是什麼?要從事什麼職業?我列出了所有想要的、不想要的,但到最後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為什麼會徬徨?因為台灣的教育理念給的是團體價值,不是個人價值,這和二戰以來台灣的缺乏自信有關。某次我訪問林懷民,他說成立雲門的最初目的,是想把舞蹈藝術帶到鄉下,但卻找不到贊助,最後他說了一句話:『到鄉下最快的路,是先到紐約。』只有在得到國際肯定後,才有可能回國完成初衷。我們一直在追求一個外在的、更高的肯定,在沒有得到這些東西前,無法做自己。」
在內心煎熬、膠著時,突破瓶頸最好的方法,便是出走到異地,遠離舒適圈的紛擾。「在異地,每樣陌生的東西都會告訴你,什麼是熟悉的。我初到歐洲時,覺得連『開冰箱』這件單純的事,都和在家時的反射性動作不一樣了。當陌生襯托出熟悉,你就會開始思考,不管是膚淺、表面還是深刻的想法,都會慢慢累積。」
出走不一定得出國,到台灣某個陌生的角落待上三五天,關掉手機、切斷網路,靜靜花時間和自己相處、與自己對話,便可達到沈澱心靈的目的。藍漢傑特別強調,認識自己最好的方式是放空腦袋、用心去感受,事物的好壞,皆由自己的體會來決定、不受他人價值影響,看見自己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找得到自己的路。

許多偶然,回頭看都是必然
曾有人問藍漢傑,為何《偶然是個魔法師》有十二個人物,而非十一、或十三個?事實上,「十二」代表十二個小時──一個時鐘的圓;二十四小時的兩個圓,則構成「無限」的符號。藍漢傑說,一般人習以「線性」的因果關係來思考「時間」,這一刻發生的事情、決定了下一刻的結果;但在許多宗教中,時間可以用「平面」來想像,不分前後、從一體來看,一件事情的發生,必然會導致對應的結果。「舉例來說,栗子樹的 DNA 並不適合台灣的氣候,因此你在春天種下,便知道它會在夏天死亡。」
任何偶然,回頭看都會發現是必然,這就是藍漢傑在書中隱隱想表達的概念。姑且不論該以「偶然」還是「必然」來稱呼世間因果的發展,如果世界上所有事物皆由一個強勢的魔法師所操控,人們又該如何面對「未知命運」的輪盤?
「李安曾說,少年 Pi 中的那隻老虎代表的是『未知』,這個未知是殘忍、不近人情的。當小男孩第一次看到老虎時,他的爸爸跟他說『你在他眼中看到的不過是你情感的投射』。就像德國人常講的”happiness is an option.“,偶然也好、宿命也好,關鍵在於你的『心』如何去看待。 」
小時候,我們總以為隨著年齡增長、經歷增加,每個人都有真正「長大」的一天,可以不再害怕,篤定地面對未知。然而,沒自信並非年輕人的專利,徬徨感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改變的,是人們面對未知的態度。藍漢傑說,年輕時總是急於找到答案,深怕因找不到方向被斥責,無法接受徬徨帶來的焦慮;現在則明白了未知永遠會在前方,可以坦然面對。至於「宿命」到底是什麼?藍漢傑認為,命運沒有幸或不幸之分,只要把所有際遇都當作生命的自然現象,像看待一棵樹的成長一般來面對,便可豁達地接受所有安排。

談及未來規畫,藍漢傑笑說自己仍像是個徬徨的年輕人,永遠無法預測生命會如何發展,能夠肯定的是會持續地創作,因為提筆為文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寫作《偶然是個魔法師》的過程也讓他明瞭了自己與創作間的關係,「創作就像一個有機體,是會自己成長、開花的。對我來說,創作是必然的動作,不然生命就不完整。」
當採訪進入尾聲,藍漢傑將一只白色信封從資料夾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交到我手中作為紀念。小心傾倒,一顆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樹栗子、一片柏林椴樹葉、一張巴黎地鐵票輕輕落入手中,成為短暫相遇後的珍寶。撰稿此時,我突地又想起藍漢傑那句:「事件會在腦中留下某些線索,只要觸碰某些關卡──可能是味覺、嗅覺,可能是一片葉子,就會重新想起回憶。」這個炎熱的台北午後,作家用願與人相知的真誠、珍惜緣份的心意,為記憶留下了具形的線索。多年後,當我再度打開這只信封,必會再次看見「偶然」魔法師於心中留下的足跡。
作者:藍漢傑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3 年 08 月 0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