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飄蕩不定的愛情面貌──專訪劉梓潔《親愛的小孩》
作為女人,從二十歲的年紀飄蕩至三十歲,劉梓潔透過〈父後七日〉重新描繪台灣鄉土的面貌,並以電影改編劇本〈父後七日〉榮獲金馬獎,如今累積近十年小說作品所出版的《親愛的小孩》,以同名篇章開啟了都市生活中男男女女包藏其中的情愛故事。
飄蕩不安的關係與生命狀態
訪問開始前,劉梓潔笑著問說:「妳呢?妳最喜歡哪一篇小說?」我說大概是〈禮物〉吧,她露出了饒富趣味的笑容,問及她自己最喜歡其中的哪一篇,她苦思了一下,最後說道:「人都是喜新厭舊的,〈禮物〉是最新寫的,所以大概是它,另外就是〈馬修與克萊兒〉。」
〈禮物〉是十篇小說中,篇幅最長、近兩萬字,接近於中篇小說的一篇,小說裡所觸及的代理孕母議題,透過劇情的轉折,幻化成能量驚人的戲劇故事。只是在當初寫成時,苦無可以發表的管道,最後在《皇冠》雜誌上分兩次刊出。編輯成書後,與在《短篇小說》雜誌刊登的〈親愛的小孩〉一齊以女性與生育之間的關係為這本小說拉開了序幕。
「其實書名本來想要叫做《搞不定》的。」在〈搞不定〉裡,講述著男人老K 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勾勒出了較為完整的男女關係面貌,也是許多人在讀過《親愛的小孩》後十分喜歡的一篇。每一個與老K 交手過的女人,彷彿與身邊的女性友人有著相似的境遇。「我觀察到身邊朋友在感情上、關係上這種不定的狀態,這似乎是現代的年輕人多數會遭逢的情境,只有部分很幸運的人才有可能從一而終。自己跟身邊的人從大學開始便經歷著對象的變換、持續的探尋,所以我就會特別去關注這種飄蕩的、不安的、不固定的感情以及生命狀態。」

除了描寫男女情愛,劉梓潔也描寫都會中的女子對於「生育」的可得與不可得、被愛與不被愛,伴隨著不同的議題諸如借精生子、代理孕母題材。談起書寫這樣的題材,劉梓潔說道:「有些故事只是沒有被寫出來而已。」在書中看似前衛的代理孕母、砲友關係,相較於現實人生的荒謬,似乎並不足以與之抗衡。「新聞中、通俗劇中這些議題都曾經出現過,有些甚至前衛多了。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會希望能夠把這些通俗的事物寫出來,像〈父後七日〉也是如此。並不一定寫鄉土就是俗的、不一定要用鄉土的腔調去寫,同樣地,在寫愛情的故事時,也並不一定都要寫成羅曼史。」
沒有愛的性
「愛。什麼是愛?愛與性可以分開嗎?如何觀察一個男人對妳只有性還是有愛?」在〈親愛的小孩〉裡,劉梓潔直指愛與性的核心。
談起書寫的取材,劉梓潔是以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們出發。「很自然地,三十歲之前並不會去思考這些事情。」因為就讀師大,在生活周遭有一部分是擔任老師、成家立業後安居樂業的女性,另一部分是在台北都會圈、文化圈中走跳,感情觀傾向於單身、不想要固定關係的女性。從這兩者上她看到了不同的生命樣態,也令她回頭思索「生育」這件事在現代所具有的意義,「生小孩首先要有性,但是我們現在的性都不是為了生育而產生的,有性而沒有小孩、沒有愛的性,回到最根源去剖析,然後我會用很好笑、很嘲諷的方式來解釋這件事情。」
對於生育,劉梓潔坦言,「再過幾年,如果我成為一個媽媽,可能就再也寫不出這樣的題材了,是在現下這個迷惘、邊緣的時刻,才能創作這樣的題材。」從她對於周遭朋友的觀察,她發現無論原本是決定要怎樣浪跡天涯的男人女人,在有了小孩後,都會因此而安定下來,而這樣的轉變,也只有置身其中之人才能體會,就連她,都難以說得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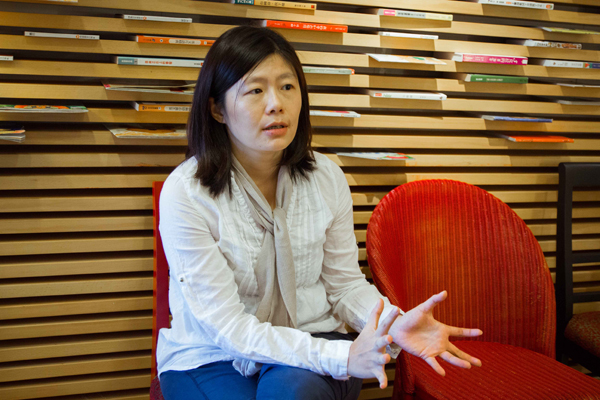
小說與劇本之間的界線
劉梓潔的小說讀來有著流暢的敘事、戲劇化的轉折,每一個畫面以及角色的互動彷彿都是一個電影鏡頭。談及作品的通俗與否,劉梓潔說道自己在書寫時是不會去思考的,「就像〈父後七日〉後來被當成一個通俗作品,但當初在文學獎時是被視為藝術性高的作品。這其實是透過讀者來決定的,當大眾能夠通過作品有所共鳴的時候,可能就會產生較為通俗的樣貌。」面對通俗性與文學性,劉梓潔以料理來比喻,眼前的料理有著不同的樣貌,紅燒的、蒸煮的,但拆解到最後,其實放在眼前的,都是同樣的一盤食材。「所以這些小說拆解過後,其實就是很簡單的內容以及想法。」
不只是小說,劉梓潔也寫劇本,只是小說與劇本之間其實有著極大的差異。「劇本是服務性質的,為了電影服務的劇本,在寫作上是有格式的限制的,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格式不重要,但其實格式會限制思考的方式。」劇本中的對白、場次銜接,劉梓潔會讓小說幫忙劇本,「但是不能把劇本寫成小說」,反之亦然,把界線盡量畫得清楚,但本質上會讓小說與劇本互相幫忙。
「像現在〈親愛的小孩〉就在改編成劇本,但會是完全不同的樣貌。」原本僅有一萬字的篇幅、一條主軸,變成劇本後會有五、六條線。「例如現在只是一個想要借精生子的熟齡女性,但在劇本中,會有不孕症的夫妻、意外懷孕的夫妻,會比較像一個對於生小孩整體的圖像。」

忠於自己的身體以及心靈
在《父後七日》之後,劉梓潔出版了一本關於旅行的散文集《此時此地》,裡頭書寫她通過旅行、瑜伽上的身體鍛鍊所帶來的改變,並不只是生理上的,在寫作、心靈上也有了一定的轉折,而在《親愛的小孩》中,瑜伽與身心靈也在其中佔據了部分篇幅。與瑜伽的關係始於劉梓潔擔任編輯的二十五歲,當時因久坐而腰痛,接觸了瑜伽後不藥而癒,她說:「瑜伽其實跟寫作很像,瑜伽是你要很忠實、忠於自己的身體,今天身體沒有準備好的時候,許多動作是做不出來、甚至是會受傷的。寫作也是這樣,在拿捏一些題材時沒有準備好,所寫出來的東西是會垮掉的。」談及瑜伽在身體上的鍛鍊,是會不斷磨練,從身體帶到思考上,對於寫作的人而言是會反應在作品裡的,「就是一個『真』吧,會讓讀者讀到我的東西時是很真實的,這可能就是根源於此。」
談起十年之間的寫作,劉梓潔說自己其實是一個相當懶散的寫作者,「但是寫作對我來說是快樂的。」過去的她是喜歡寫作、採訪,但並不認為自己是名「創作者」,轉折點在於〈父後七日〉獲獎、改編成電影後,使得創作本身足以支撐生活,她才能夠更專注於創作上。
在小說創作上,她以香港作家陳冠中在《南方人物周刊》中的採訪為例,陳冠中認為小說家分兩種,一種是類型式的,會做好資料準備、做功課來寫小說,另一種是一定要有了生活經歷才能寫。「我過去大概是屬於後者這種,也有人說是『本色』作家,就是『本色演員』的意思,只能夠演他自己,但我現在漸漸會逐漸往第一種小說家走去,以技能為主,只是也不會擺脫第二種,有些情感是需要自己體會過的。」

提及未來的寫作計畫,劉梓潔說正在構思關於心理與精神療養相關的中篇小說,以及以家族史為主軸的故事,只是依舊在等待著故事成形。從散文到劇本、小說,劉梓潔用說故事的方式道盡了浮世眾生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