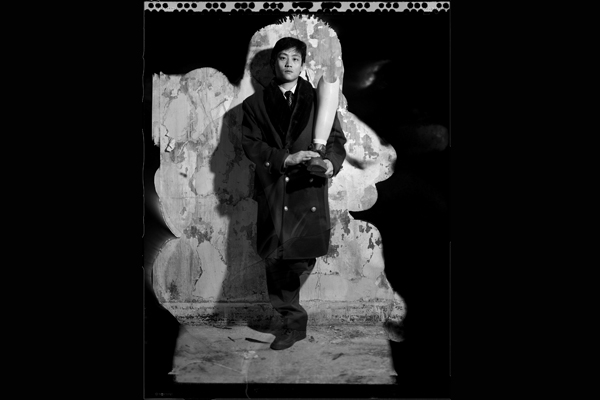蘇育賢《石膏鑼》:穿越存在主義,敲擊破碎的肉身
蘇育賢於七月在耿畫廊展出了這兩年透過《劇場》雜誌研究與調查的作品,作品包括錄像、文件與石膏鑼的再製物件。這些作品聚焦在當時黃華成及其人際周邊的藝文現象。以此為起點,蘇育賢打開了一個當代藝術追溯歷史事件的契機。透過了當時黃華成的一些戲劇表演,帶領觀眾回看這個事件,並從綜合藝術的劇場提萃出當代藝術的另類歷史。
誰是黃華成呢?總地來說,黃華成在臺灣上世紀中葉是個異數,重新引介存在主義戲劇的思想來到了臺灣。1965 年黃華成與《劇場》雜誌的同仁演出了《等待果陀》,也曾編寫帶有荒謬劇色彩的《先知》。《先知》在當時迫仄的政治環境下描述了寫字員的卑微與經濟困難的現實,這個作品也顯露了六零年代台灣詭譎的政治狀態。《先知》彷彿戲劇史送給藝術的禮物,在這個展覽中蘇育賢透過了《石膏鑼》接收的圖像,在個人詮釋與經驗的兩個軸度上回顧了這場戲劇作品可能的潛力。
|
|
 |
《先知》:知識份子的虛無與緊張
《先知》所寫就其當時寫字員的存在,在電腦發明之前仍是維持公文系統的系統組成。「謄寫文件但社會地位不高的職業」成為黃華成筆下表達當時知識份子虛無氣氛的面貌,這樣的角色一方面有著現代文學常見針砭官僚一成不變的責難,同時這個故事又參雜了傳統中國懷才不遇的主題。這兩者結合的實驗劇作,曾找了演員莊靈與劉引商在耕莘文教院演出此表演,後來蘇育賢的作品也邀請了原班人馬再次演出。
除了此劇接受了當時存在主義思潮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六〇年代正當台灣推動中華文化運動時,耕莘文教院作為文學飛地成為了當時現代主義的重要空間。當蘇育賢《石膏鑼》個展中,重新地演出了《先知》。除了藝術家的意圖之外,這在當時與國民黨政府保持一定良好關係的耕莘文教院,也有著文學條件的潛流慢聲流過這個作品。
將黃華成的角色拉回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我們已經在黃華成《椅子》的裝置作品搭建出字彙與物件的雙重關係看到其魅力。詞彙與物件交織的張力,是帶有圖像學傾向。《石膏鑼》的展覽裡頭,石膏鑼的起源──蘭克(Rank)為電影的敲鑼人,蘇育賢將之視為一種被錯失的意識或說潛意識,轉換成為探索台灣戰後現代性的一種可能。
影像的再譯:當觀者不再忠誠
原本黃華成《先知》的劇本是描述一對夫妻前往觀賞舞台劇,但舞台上卻只有布幕運動及滑輪聲響等光影與聲響,整個演出設定男女主角在觀眾席上對話。這是未曾付諸實現的劇本,蘇育賢這個作品可以說才真正的實現黃華成的願望。物件的模擬與其詞彙上的互動在黃華成長期作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蘇育賢透過歷史事件的再生產生了某種繼承。《先知》劇本預定以動力機械表演,到更後期,就如同字典等同一種事物的收藏體系,讓黃華成到蘇育賢的重演過程中,敲鑼人帶圖像性(iconicity)穿越過藝術家對於前衛的詮釋與經驗 。
採用雙頻道方式,蘇育賢讓黃國華最初版本的演出重生,讓觀眾有機會在觀影的方式選擇兩個版本其中一種。換句話說,在錄像的佈局上,演出是莊靈與劉引商是在幕下演出,但對觀眾視覺的選擇仍可採取傳統的戲劇觀看位置或是黃華成原本的預設。
觀眾本身的選擇成為了兩種時代的不同演繹。是的,觀眾的身體回到了《先知》原本預設驚訝感所能造的震撼,65 年的版本或是劇本預設的版本從被驚嚇的主體變成今日自由的身體。觀眾身體的狀態受時代左右顯而易見,但也生成了前衛與藝術自治的主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家與群眾互補的狀態,兩種主體性在不同社會條件下關於版本叛逆與忠誠的不同位置。卻也弔詭地,可以看到演員勞動的身體,在時空中被遺忘、衰老的差異,前衛的肉體並不等待觀眾保持年輕,有其藝術本身代謝的周期。
聽見藝術史邊緣的慾望
展覽中縱使陳映真的角色在錄像紀錄中透露著左翼立場面對西方思潮的部分質疑,但敲鑼在文化上的殖民現代性中,黃華成與蘇育賢的「石膏鑼」的使用卻相當地不同。在《先知》裡頭,我們看到石膏鑼在當時的使用是做為仿擬物,當時由陳映真敲碎的石膏鑼,其機制乃是透過了舞台式的視覺機構,將視覺與聲響的連結打斷,在首演時提供騙術般震撼的戲劇效果。
蘇育賢的使用則是鑼「聲」,他利用了兩支錄像,解釋了石膏鑼的相關人員及其製作過程以及拍攝出石膏鑼發出的各種聲響與敲擊承受力。透過了這一場被藝術史邊緣化的事件,《石膏鑼》暗示一種社會潛意識的存在,試圖將陳映真敲鑼的過程視為一種被邊緣化的主體發聲慾望。
但更需要被指出的,這種被壓抑的力量並不僅僅只有保守的閱讀環境,而是放在六〇年代,美新處與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抑,這些前衛的力量相對地更顯隱形,使得北台灣耕莘文教院的特殊性更為突出。個人詮釋與經驗兩種意義的張力在這個展覽中是有所抉擇的。
從石膏鑼看劇場的內在分裂與流變
1965 年黃華成、邱剛健、莊靈、許南村(陳映真)、劉大任等《劇場》雜誌團隊成員的內在分裂,在《石膏鑼》也就不僅僅在於還原石膏鑼從發想到製作完成的過程。
無形中,這塊石膏鑼一方面是從鍋蓋到鑼的形像上的意義、是對於劇場形式轉變的意義,也是記錄上的重生。這三種意義呈現了藝術史學家 Panofsky 所提過「圖像學的三重意義」。在文本與視覺之間的拔河,成為重思台灣本身的思想布局為何在戰後強烈壓抑了前衛的可能。這在文學中也有著同樣失落的現象。在這裡「石膏鑼」更接近 W.J.T Michell 在討論圖像性時將之回到了圖示的邏各斯(Logos),蘇育賢《石膏鑼》與黃華成《椅子》在這裡就有著相似之處。
但更重要的是《石膏鑼》除了「這是石膏鑼」、「這不是石膏鑼」之外,更直接說出了不只是一個石膏鑼。透過了四組藝術家的敲擊、聲響、破碎的形式,石膏鑼的家族相似性也讓《劇場》發生的內在分裂有更多的陳述空間。
透過石膏鑼這個圖像性的延伸,也存在看不見的標準化運作,無論是其起源與蘭克公司的關係,或是石膏鑼有其仿製的方式。其生成的貌似性,在展覽中不同方式的增生與仿擬,以及從《等待果陀》中汲取的現代性是如何被重新消化成為台灣的一部分,足以讓我們改寫傅柯的句子成為:「前衛主體以徹底的方式體驗它自己的世界」。
|
|
|
|
|
|
石膏鑼──蘇育賢個展
展覽期間:2017.07.08-2017.09.10
展覽地點:耿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