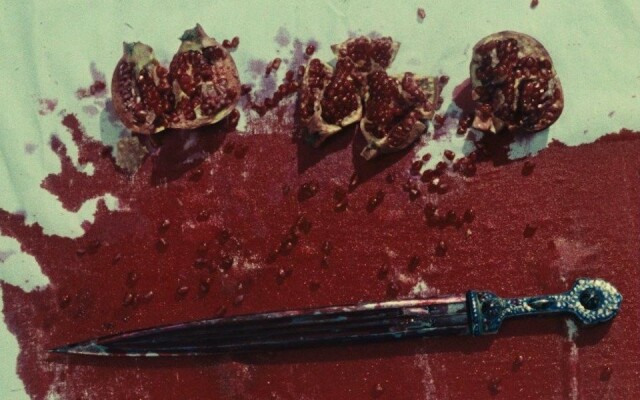什麼是當代藝術?專訪徐冰:沒人說過的話才值得去說
走進夏日的中山堂,外頭暑氣頓時被這巨大而歷史悠久的建築給吸納,在會客區一隅,徐冰戴著招牌圓框眼鏡正閱讀著手機,見我們到來,不疾不徐地起身打招呼。前一日剛抵達台北,今日接連兩檔採訪外加晚上一場講座,行程滿檔,問起有沒有時間在台北逛逛,徐冰笑說他幾乎都在忙工作。這次來台灣是快閃行程,隔天就要回北京籌備月底開幕的回顧展「徐冰:思想與方法」(註),現場還有許多細節需要處理與確認。創作四十餘年、類型廣泛,無論是展覽或專訪,要呈現其「思想與方法」都不容易。但當他真的開始說起創作思想與方法,應答的從容與淡定讓人不禁感覺:或許一介當代藝術大家的高度,實則出自對所有創作環節透徹的思考、體會,沒有一絲僥倖與閃躲。
徐冰不是一位可以被定義的藝術家,至少不是透過使用的媒材來定義。他傾向認同自己為觀念藝術家,觀念是否清晰、創新、沒有破綻,是他在開始創作前便會沙盤推演清楚的。如同這次在台北電影節放映的《蜻蜓之眼》,他的作品時常曠日費時:「一個概念的發想,我可能會放個好幾年,也可能隔幾天就開始,但重點是我一旦要開始做,就會把每個步驟想得很清楚,我不是那種邊做邊想的人,因為我很怕到後來兩個東西無法串聯在一起;好比建築的接榫要怎麼接,那是建築師得要事先想清楚的。」
 |
訪談裡他說起創作想法皆條理分明,不需追問也能完整回答,步調和緩有餘裕,無疑是「想清楚」了才行動,絕非為了發言而言,為了創作而做。藝術有時勞師動眾,有時耗費心神,對徐冰來說如此代價有需要回應的目標:「我認為藝術家便是要以藝術的方法,回應當代的問題。」
拼貼監視器與直播,影像版當代《清明上河圖》
《蜻蜓之眼》是徐冰執導的首部長片,說是執導,但他也絕非多數人所熟悉的電影拍攝方式。在 81 分鐘片長裡,沒有一格畫面是指導演員演出、指導攝影師拍攝的,整部影片皆是徐冰與他的團隊花費將近兩年的時間,從各地的攝錄影機,包含街上的監視器、直播畫面、行車紀錄器等各種上傳至網路的影像剪接而成,沒有攝影師、沒有演員,工作室有的是 20 台 24 小時不斷下載影像資料的電腦,而下載來的影像由團隊成員依照各種關鍵字加以分類,比如北方的寺院、南方的寺院、一位尼姑等。這樣的工作從 2015 年開始持續進行,一共蒐集了 1 萬 1000 小時的畫面資料庫,居然讓徐冰拼貼出一個有劇情的故事。
《蜻蜓之眼》的手法特異,卻是一個關於「整容」的古典愛情故事。為什麼是「整容」呢?徐冰說作為一位觀念藝術家,他想做的電影,是想要挑戰傳統敘事電影的作法,舊有的電影概念對《蜻蜓之眼》而言是無效的,他要刺激人們既有的思考。因此他為自己設下了目標,整部電影不能有一格畫面是自己拍來的,必須要是從網路上找到的,也因為是不同來源的畫面、並非同樣的人物,所以必須面對與處理如何讓故事的推進合理的問題,如何讓角色連戲,就成了一項功課;於是,講述一個「整容」的故事,便成為在現實條件下的設定。但同時,這樣的題材卻也恰好呼應徐冰藉由蒐集、取用監看畫面所試圖探討的——到底我們表面看見的和真實的,彼此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
| 徐冰《蜻蜓之眼》(2017)劇照。 81 分鐘彩色有聲劇情長片。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
| 徐冰《蜻蜓之眼》(2017)劇照。 81 分鐘彩色有聲劇情長片。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2013 年,「以監視器畫面來拍一部電影」這想法便已在徐冰的腦海中浮現,然而當年的技術條件尚未符合,可取得、下載到的監視器畫面、直播畫面並沒有那麼多,但到了 2015 年,這類的視頻影像俯拾即是,影像的泛濫,讓徐冰相信以這樣的方式拍出一部長片,是可能的。於是他依據編劇翟永明、張憾依寫的劇本去尋找合適的資料畫面,也會因為一些有意思的畫面,回過來修改劇本,那過程便是一來一往有機的拓展與調整,最終找到一個可以最大限度使用這些材料的版本,而不讓一絲有意思的材料浪費。「甚至會有目的性地追蹤、鎖定幾個場所的攝影鏡頭,比如整容診所,我們知道他的門口有個監視器、大廳也有一個,到了二樓還有一個,監視器的豐富正好幫助我們敘事更完整。」徐冰神色淡定地說著。
然而,《蜻蜓之眼》談的不只是監控,還有影像的傳遞、影像的交流、影像作為一種技術的手段,如何被世界所用。這是持續在發展的過程:「『監控』的概念迅速在變化,快到讓我們無法判斷到底什麼樣的觀看是『監控』。例如現在隨處可見的網紅直播、行車記錄器,過往談的『監控』其實是幾十年前冷戰時期的那種『老大哥式監控』,但在當代幾乎不適用了。今天的監控技術有很大一部分被民間掌控,人人都使用這技術來為自己服務或改變命運,但舊有的概念卻無從判斷。」
徐冰談及《蜻蜓之眼》中使用的網紅直播橋段——男主角柯凡入獄與愛慕的女主角蜻蜓失聯,後來看到網紅瀟瀟直播的畫面,相信她是整容後的蜻蜓,於是在直播平台上展開熱烈的追求。然而瀟瀟是否就是蜻蜓,其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徐冰透過這樣的畫面,呈現出他對於當代此種影像傳遞方式仍在反覆辯證的思考進路:「直播是不是一種『監控』?人們直播時一直希望表現出自然的自己,但是我們都知道那樣的狀態絕非自然的,然而這又跟在電視台上主持不一樣;那透過直播呈現的我們跟真實生活的我們有什麼不同?或許像演雙簧一樣,有些刻意讓手機畫面裡的我們說,有些是留給真實的我們。」
 |
 |
正因為這些影像天生具備了某種紀實的性格,每一格畫面都是真實被記錄下來,是存在且實際發生過的,使其荒謬性在某些時刻更加強烈,例如《蜻蜓之眼》中幾幕飛車追撞的暴力事件,讓人看得怵目驚心。而徐冰和其團隊也因著大量目睹各地的監控畫面,到後來出門都特別小心,「因為意識到這世界是無法掌握的,任何時刻都可能發生任何事。」
「有次我們需要一個下雨天車子從山路駛過的畫面,於是先查了天氣預報,知道何時會下雨,就鎖定一個時間段的監視畫面,來找出有車子駛過的時刻。」將這些具有紀實性格的畫面,經過特意挑選後剪接成劇情片,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來回辯證相當令人玩味。徐冰運用這些素材的方式,像是在為一幅巨大的《清明上河圖》般的作品尋找合適的元件,畫中的人事物絕非在同一時地出現而被素描紀錄,而是畫家四處採集風土民情、庶民生活,將之符號化,作為那時代某種生活樣態的代表,勾勒當代生活。
於是,《蜻蜓之眼》裡出現的人物、景致、物件,例如從路上駛過的車子、寺院裡的僧人、穿著制服的公安、在電腦前與人聊天互動的青年,無不像是某種符碼般的存在,象徵性意義大過個體實存意義,裡面的人物與街景都去個體化、去識別化,無意讓人判別,就如同中國繪畫的「象徵性」與「符號性」,畫一座山並非是寫實描繪那座山,而是以一座山代表群山,以一棵樹代表森林,是一種意象的表達。
當我們看見這些意象,所謂敘事也不再單純:「表面上以劇情長片形式講述一個古典愛情故事,但實際上真正要說的並非故事本身。我覺得這就像中國傳統的『聲東擊西』——我看似跟你說這件事,但其實我真正要說的是另一件事。」透過這些資料畫面的蒐集,徐冰實則拼組出一幅長達 81 分鐘時間軸的當代「風土民情長卷」,呈現紀實影像氾濫卻關係尷尬的當代:「如果監控影像能夠完成一個相對複雜的敘事,那麼這就說明了監控影像和我們社會的關係。」
 |
非常認真做荒謬的事,才有藝術的力道
從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庫中調閱出有用的材料,那是多麽繁浩的工程,但徐冰似乎早就對這樣「勞力密集式」的工作方式習以為常,綜觀其過往的作品《天書》、《地書》甚至是更早期的版畫作品《碎玉集》,在工作方法與概念上都有本質上的相似之處。
例如《蜻蜓之眼》的采風性質,《碎玉集》在將近四十年前即以一種樸實的方式呈現過。這是徐冰結束文化大革命時期「知青插隊」到中國北方農村生活和勞動後創作的版畫作品集,他在進入中央美術學院後,於 1979 - 1985 年之間完成一百多件掌心大小的木刻版畫,勾勒他在農村觀察到的生活采風剪影。《碎玉集》不僅譜出一部時代的中國農村生活錦集,這作品更是徐冰訓練自己木刻刀法的圖譜,試驗了他所見識過的中外木刻刀法。
「版畫」是徐冰早期重要的創作形式之一,與版畫有關的「複數性」、印刷、印痕,可說是縱貫其創作的重要節點。徐冰的母親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服務,從小他就常在圖書館裡待著,隨手翻閱書籍,因此對書的手感、裝幀方式、字體結構有著高度興趣,日後在版畫創作中找到出口;版畫印刷產生的印痕有種「被規定性的美感」,自帶完整性,而這種完整性,正好滿足了徐冰追求完美的性格,且版畫對勞動與耐心的高度需求,得手工一刀一劃完成,這如工匠式的手作精神,也一再出現在徐冰的作品之中。
雖然版畫是種傳統的訊息傳遞技術,但徐冰對其「複數性」的思考卻是相當當代的,「『複數性』與工業化生產和標準化緊密相關,當代是『去個性的』,每個人身材不同,但是坐的椅子卻樣式一樣。到最後原作和拷貝沒什麼差別。」這種不斷複製的特性,更是構成其視覺力量的來源。某種程度而言,徐冰的《天書》之所以令人嘆為觀止,也正是建立在「複數性」的特質上。
《天書》是徐冰最知名的作品之一,顧名思義,《天書》就是一本無人看得懂的書。它雖然具備了書的形象,內文也像是中文方塊字,但那些文字都是徐冰依照《康熙字典》的筆順一個個創造出來的假字,一共 4000 多個假字,看起來像中文,但實際上又不是,內容是空洞的。當時是 1987 年,他才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一心想做一本「看似說了很多事情,但其實什麼也沒說的書」,徐冰立定明確想法後便開始動手將那些假字刻成木頭活字。他一個人花了一兩年刻出了上千顆木頭假字, 然後又費盡心思為假字研究排版的方式,找到合適的印書廠,煞有其事地從沒有內容的假字中挑選了三個最像漢字的「字」作為書名,每頁書頁也加上頁碼、序號,最終印製了 120 套,每套四冊,一共 604 頁。
|
|
| 徐冰《藝術為人民》(1999) 材料:綜合媒材裝置;旗幟、電腦噴繪。尺寸:11 x 3 m 地點: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1999;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2001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
| 徐冰《天書》(1987-1991)。 媒材:綜合媒材裝置;活字版手工印制書籍和卷軸,漢字的部件重新製造的「偽漢字」。 地點:台灣,台北市立美術館,2014。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當大量的木刻字、書頁擺在眼前,其「複數性」便是其視覺力道的來源;當假戲真做到一個程度後,其荒謬性就會凸顯,「我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必須非常認真去做這本書。一旦非常認真,它的荒謬性就會很強,自然會產生某種藝術的力度。換句話說,『認真的態度』是《天書》這作品的藝術語彙和材料。」徐冰憶起《天書》的創作過程時說道:「做《天書》時,我一心想著要做當代藝術,但當時人在中國,對當代藝術的概念與文化訊息並不充足,在那樣貧瘠的情況下,身上有什麼,就表現什麼,這就是藝術的誠實性。所以《天書》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都是相當具有中國傳統哲學意味的,是透過不溝通來達到溝通,就像中國禪宗。」
當代藝術,應該要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九〇年代初期,徐冰前往美國紐約,正巧接手艾未未在東村七街 52 號地下室的公寓。在紐約時期,徐冰面臨了文化衝擊,因而產生《英文方塊字》這件作品。這作品延續著其對書法、中文字的結構研究,以類似書寫中文部首偏旁,創造出「方塊字版」的 26 個英文字母;看似中文,但實際上卻是一套新的英文書寫形式。徐冰為了這套文字系統,設置了讓觀眾參與的語言教室,裡面有教科書、有字帖,觀眾可以臨摹這套文字的書寫方式。《英文方塊字》不像《天書》是沒人看得懂的偽文字,它是有其文字結構邏輯的,簡單來說即融合了英語的拼音邏輯跟中文字的書寫結構,每一個英文字母對應到一個「類部首」偏旁,堆疊組合後即為一個單字,有點像春聯「招財進寶」那種組合字。一旦懂了這套邏輯,它是可以被讀懂的,只是它同時具備了英語和中文的文字系統。
作品反映了徐冰身處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處境與思考,也顯現所有遠渡重洋、試圖融入美國文化的華人困境與意志。這是徐冰眼中,當代藝術家的任務:「幾乎沒人說得清楚『什麼是當代藝術』,我認為當代藝術應該要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且對社會有益處、對人的思考有啟示,對人們思考的盲點有調節作用,才值得去做。對藝術家來說,工作動力來自對社會的敏感,以創作來表述對社會的態度,而這種表述的方式是過去沒有的。沒人說過的話才值得去說。」
.jpg) |
《地書》則是另個相當有趣的嘗試,這是一本由各類圖示、標誌、符號寫成的書。從 2003 年開始,徐冰因為口香糖包裝紙上的三個圖示(示意著嚼完要包在紙裡丟進垃圾桶)而受到啟發,「如果這三個圖案就可以說明一件事情,那麼眾多圖示組合在一起,就一定可以說個長篇故事。我在思考的是,圖形符號作為文字,到底能表達到什麼程度?」
於是徐冰便開始展開大量的圖示蒐集與累積的工作,與《蜻蜓之眼》採集圖像的過程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限定自己這些圖示必須是「蒐集來的」,沒有一個是自己設計、發明的。對徐冰來說,「蒐集來的」表示它是實存的、甚至約定俗成,圖像式的閱讀具有文化通用性,相較於《天書》是無人看得懂的文字,《地書》反而是任何人都看得懂,「它不對位於任何已有的文本知識,而直接對位於真實的生活邏輯和事物本身。對這些符號的識讀能力不在於教育程度,而是取決讀者介入當代生活的程度。」兩者的共通性便是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端看觀者如何去理解、解讀,思考並享受那閱讀的經驗。
.jpg) |
| 徐冰,《英文方塊字書法教室》(1994-1996) 材料:綜合媒材裝置;錄影帶,黑板,課桌椅,筆墨書寫用具,教學掛圖,習字帖。 尺寸:隨布展需求改變 地點:昆士蘭美式館《第三屆雅太地區當代藝術三年展》,澳洲布里斯本,1999。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jpg) |
| 徐冰,《地書》(2004 至今) 版權所有:徐冰工作室 |
我們如何度過時間
雖然創作生涯有頗長一段時間待在紐約,並且身處以西方為首的當代藝術領域前沿,但徐冰的創作始終根植於自身的文化背景,特別是中國傳統的書畫。但他並非鑽研傳統書畫的形式,乃是取其造型與原理,作為思考的原點與度量,重新測度自身文化與當代藝術間的關係。
「我的創作動力,來自一種原始的生命動力。我認為人最核心的命題,便是如何『度過時間』,把時間用掉。那把時間用在什麼事情上,就是考驗一個人的關鍵。」訪談到後段,徐冰略顯疲倦,但說起話來依然條理分明、思慮縝密,同時又帶有興許是歲月積累的從容。他從事當代藝術創作,但卻自有一番東方哲人式的思考,以及堅持親力親為的職人性格。
像他以倉頡造字的精神,做一些無端荒謬的事,貴在全心全意而為:「我習慣的工作方式是,若我認定這個想法值得做,那我就會全力以赴的去做,對我來說,這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初動力,來自我想看看概念設想跟最後結果會有多大的出入?因為沒人做過,也就無人能告知。就像做科學實驗一樣,得將各方面的變因都掌握到最好,沒有浪費或遺漏,若過程中沒有掌握好,可能本來能達到的卻無法達到。」
聽著他語氣平穩地說了這番話,想到《天書》、《地書》、《蜻蜓之眼》這類浩繁龐雜的作品,尚未回過神,徐冰又添了一句,「我是那種展覽開幕前一刻,還會在展場調整燈光的人。」即使擬定女媧補天般的龐大計畫,卻也不吝在最小的地方度過時間,或許這就是徐冰的藝術能不斷刺激當代的我們的原因。
 |
編註:「徐冰:思想與方法」回顧展已於 7 月 21 日開幕,詳見活動官網。
*本文特別感謝台北電影節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