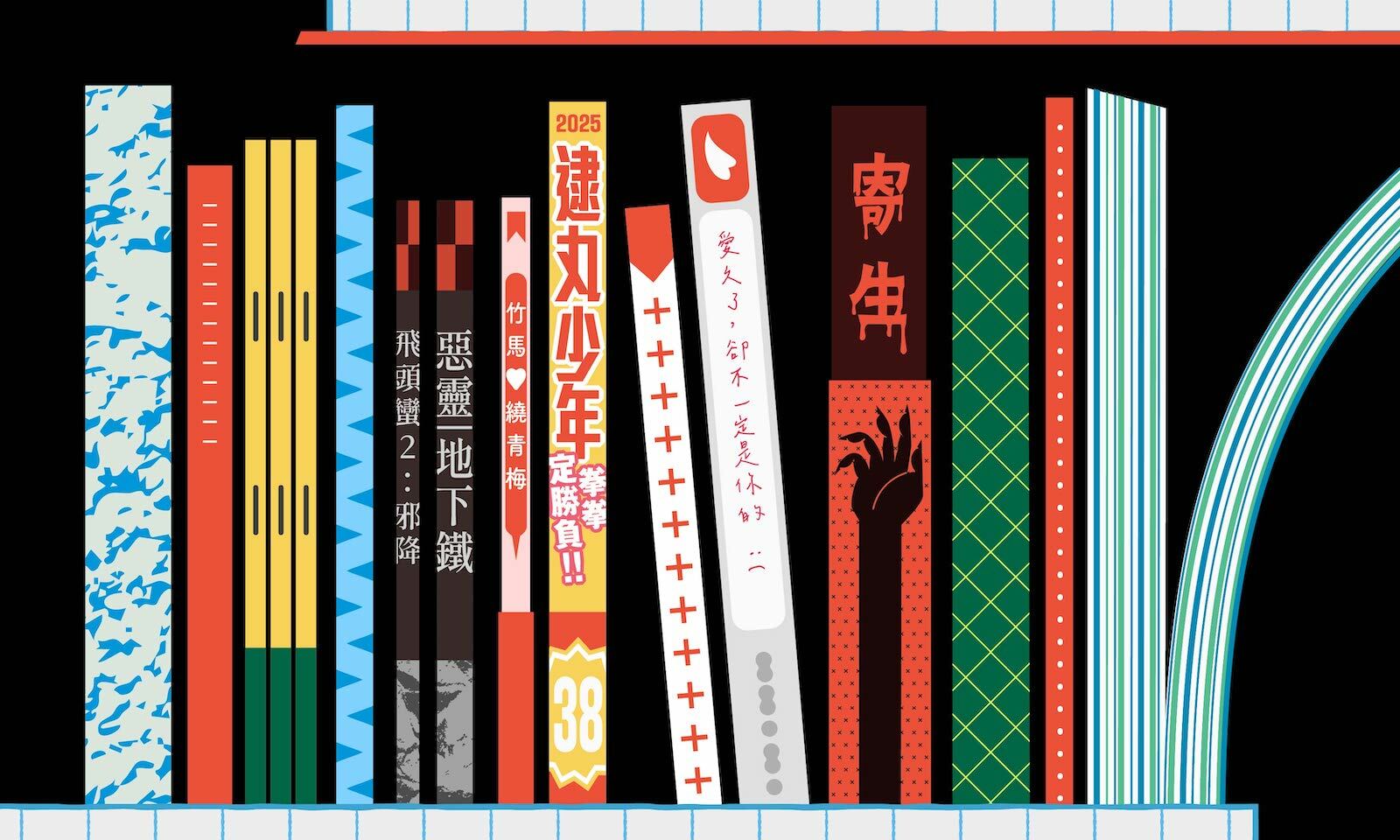
那一年,便利商店開始賣書了──超商書架上的前世今生
即使不曾在便利商店買書,記憶中或許也還留存著這樣的場景:學區附近的便利商店,剛下課的學生徘徊在壓克力貨架前,抽出一本明日工作室最新上架的 49 元恐怖小說,隔著塑膠膜看清楚簡介,接著小心翼翼地拿著 50 元銅板去結帳。
十年過去,49 元小說書架已經消失,其餘書籍也逐漸退場,貨架上只剩下三三兩兩的出版品。過往那些曾讓我們駐足的故事,如今只模糊地留在記憶裡,彷彿千禧年間的一場幻夢。現在走進便利商店,疑問偶爾還是浮上心頭:究竟是從何時開始,這些小說從便利商店裡消失了?或是再往前追問,它們最初是如何誕生的?
根據曾任國家圖書館書號中心主任的曾堃賢研究,1988 年,7-11 首開書籍銷售,隨後各家便利超商紛紛跟進。那是解嚴以後,圖書出版題材百無禁忌的年代,出版法廢止後,出版社數量隨之遽增,書報攤等傳統攤位也逐漸被更貼近消費者的便利商店取代,在超商貨架前看書與雜誌,自此成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那時的便利商店貨架,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書種:理財專書、醫療保健類書籍長年穩居架上,學區附近的門市擺著瞄準學生族群的《名偵探柯南》、《火影忍者》漫畫單行本或輕小說;而網路文學小說興起後,橘子、九把刀的新書也開始在便利商店販售,有時甚至會在架上撞見張大春等純文學作家的作品——早在九〇年代,出版社就曾經嘗試打破便利商店與純文學間涇渭分明的界線。
兩個貨架,這是 21 世紀,文學與麵包的距離。
但對當時的出版市場而言,便利商店不過是眾多銷售通路中的其一,至於為便利商店「量身訂做」的 49 元小說,這時還沒出現。
走進便利商店,消費者想看什麼?
明日工作室前總編劉叔慧回憶, 49 元便利書的構想,是由明日工作室首先發起的——儘管台灣一直都有日本文庫本尺寸的出版形式,然而因為台灣與日本讀者的閱讀習慣差異,方便通勤時閱讀、隨看隨丟的文庫本,並不是台灣出版社的主要選擇,直到明日工作室開始在便利商店販售售價低廉的小開本小說,才開啟了千禧年後的便利書熱潮。
而便利書的誕生,其實源於明日工作室創辦人溫世仁在 SARS 期間的一次異想天開。
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台北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台灣社會陷入恐慌,溫世仁有感於當時隔離政策對人權的嚴重侵犯,於電台受訪時提出「健康者隔離」概念,主張應調整防疫策略,由尚未染疫者主動進行自主隔離。
節目播出後,聽眾反應熱烈,溫世仁於是請劉叔慧協助將訪談內容整理成小開本的衛教手冊,並與便利商店通路合作上架,供民眾免費索取。沒想到近萬本小冊上架後,在短短幾日內迅速發放完畢。溫世仁敏銳地察覺到便利商店作為銷售通路的潛力——他由此發想,是否有可能利用超商通路,發展出只屬於明日工作室的出版物?
於是明日工作室首先與全家合作,推出類似文庫本大小、以健康知識與生活資訊為主的書,並以「便利書」為名;然而疫情結束後,防疫熱潮消退,銷量並不理想。直到一次會議中,編輯們重新思考:「走進便利商店的消費者,究竟想看些什麼?」於是調整方向,轉而嘗試出版恐怖小說,沒想到銷量超乎預期。 2006 年,「異色館」系列於焉誕生。
隨著「異色館」書系成立,明日工作室開始招募新銳作者,笭菁、振鑫、蝴蝶等作者相繼加入,也為明日工作室吸引了一批忠實讀者。49 元銅板價恐怖小說在學生族群間暢銷,新書上架日總能為學區附近的便利商店帶來人潮。出版社甚至接到家長投訴,抱怨孩子對異色館小說過於沉迷,上課都在桌子底下偷看;其他出版社也爭相模仿起明日工作室的「便利書」構想,接下來十年間,便利商店出現了一波 49 元小說熱潮——在便利商店賣小說,似乎真的可行。
日後回想,劉叔慧說,是溫世仁那股極其敏銳的「未來的嗅覺」,開啟了便利書的黃金年代。
便利商店,與書
便利書,主體先是便利商店,接著才是書。
在所有通路中,劉叔慧認為便利商店因為不需仰賴書籍銷售,且掌握了大量客源,在所有通路中最為強勢,現任遠足文化副總編輯的賴譽夫也有相似的觀察。
賴譽夫回憶 2014、15 年與便利超商合作的經驗,「對便利商店而言,雜誌以外的出版品都是次要的。如果預判這本書的銷量無法接近或者超過五成,對方會說,這可能不適合我們。」
超商通路強勢、利潤低,幾乎不可能作為銷售主力,對大多數出版社而言難以長期營利,只是作為機會性配合,或是新書宣傳的途徑。為了讓書籍出現在超商貨架,出版社必須主動向超商提案、證明書籍潛力,超商有興趣,才可能進一步談合作。
當時為了讓出版社新書在便利商店上架、提升能見度,賴譽夫帶著奈良美智和村上隆的藝術特刊,親自遠赴五股與經銷商開會。
因為是圖像藝術類書籍,加上奈良美智與村上隆國際知名度高,經銷商同意了。透過系統媒合,將書籍配送到全台兩千多家門市,賴譽夫甚至曾在蘇澳馬賽門市看見特刊擺在架上——蘇花改建成以前,那是從台北到蘇花公路途中必經的一間門市。意料之外卻精準的配點,讓賴譽夫感到詫異。
超商的精準,源於對消費數據的敏銳感知。書籍定價從 49 到 299,哪些價格銷量最好?有限的貨架空間,與哪些出版社合作能帶來最大效益?進入超商通路,露出書封或書背的上架費甚至可能是不同價格。
劉叔慧記得,當時為了讓「異色館」系列順利在超商上架,明日工作室自掏腰包,為便利書設計了專放小開本書籍的壓克力陳列架。儘管銷量高,但是 49 元小說的利潤實在太低,當時也曾嘗試將售價提高到 69 元,但銷售數量果然隨即受到影響。
「我們的主力客群都是學生,對學生來說, 10 元、 20 元是很值得斤斤計較的。必須是讓讀者能夠毫不猶豫拿去結帳的價錢。」
於是便利書的價格從此便停在 49 元。為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便利書市場留住忠實讀者,明日工作室每月固定日期上架新書,短短一個月內,必須事先預告下一期作家新書、為作者安排檔期,並與封面設計配合,迅速將作品送至印刷廠。書展期間,明日工作室也為作者舉辦讀者見面會,為新銳作者培養起一群死忠粉絲——一條從便利商店貨架開始的生產線已然成形。
穩定的出版模式與忠實讀者,使得明日工作室在眾多便利書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超商業務提供的銷售報表顯示,明日新書上架的那幾天,能為超商帶來人潮、帶動其他商品的銷量。超商也察覺到了,甚至主動要求明日工作室必須持續出版銷量特別好的書種。
「便利商店是非常敏感的通路——它們是海嘯第一排。」
密佈全台,從每個街角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便利商店總是站在時代潮流前端,感應著消費者的變化。當明日工作室提出「便利書」構想,便利商店敏銳地捕捉到背後的商機。 然而 2010 年代,當智慧型手機開始進入大眾的日常,書成為「不好賣的商品」,超商也在第一時間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
兇手是 iPhone
賴譽夫觀察,約莫是從 iPhone 出現開始,智慧型手機完全改寫了大眾的消費模式。從 2010 年代開始,便利商店中的書籍銷售已經逐漸進入停滯期,直到 2014、15 年,全台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達到 7 成,社群媒體、網路平台成為新的資訊管道;當書籍基本起印量從原本過萬本降至一千多本,在便利商店賣書,幾乎已經不再是出版社的考量。
「其實原本跟超商之間就是機會性配合——對出版社而言,只有書店才是一輩子的合作夥伴。」賴譽夫總結。
賴譽夫觀察到便利商店書籍銷售開始走下坡的 2014 年,也正好是明日工作室停止出版業務的那年。
一般書籍離開超商通路後,或許還能回到書店或電商通路,然而對從一開始便為超商量身打造的「異色館」書系而言,當超商不再是有效通路,便等同於便利書時代的終結。
「兇手就是 iPhone 吧。」說起便利書的式微,劉叔慧如今也釋然:「我們和一般出版社不一樣,一本 49 元,薄利多銷的模式,原本支撐我們的就是銷量。手機普及化以後,我們沒辦法再為超商通路帶來過往的銷售數量,他們很快就察覺了。」
便利書的退場,似乎是時代的必然。昔日新書上市日總被搶購一空的異色館小說,開始滯銷在壓克力陳列架上,大量退書被運回明日工作室。這時已經不會再接到家長投訴說學生上課都在偷看小說了,曾經讓讀者沉迷的恐怖故事,如今能夠輕易被手機螢幕上更刺激感官的短影音取代。
於是在便利商店不再需要書的時代,異色館書系於 2014 年結束,明日工作室也隨後停止了出版業務。
便利書時代結束後,至今過了十餘年,賴譽夫已經離開了當時的出版社。有時他經過便利商店的貨架,還是會想,如果便利商店代表的是人們生活的日常面向,是否還有什麼方式,能讓書回到這裡?
而劉叔慧離開明日之後,也連帶向出版工作道別。便利書像是一場屬於千禧年的幻夢——又或許不只是夢。
前幾年,有位年輕警察來到她家中做戶口調查,在閒聊中得知劉叔慧曾經在明日工作室擔任主編,激動地告訴劉叔慧,他是明日工作室的忠實讀者。劉叔慧驚訝地想,原來讀者都已經長大到可以當警察了!
其實豈止警察。當年便利商店那些書的讀者,也已經長大到能夠為便利商店小說做一個專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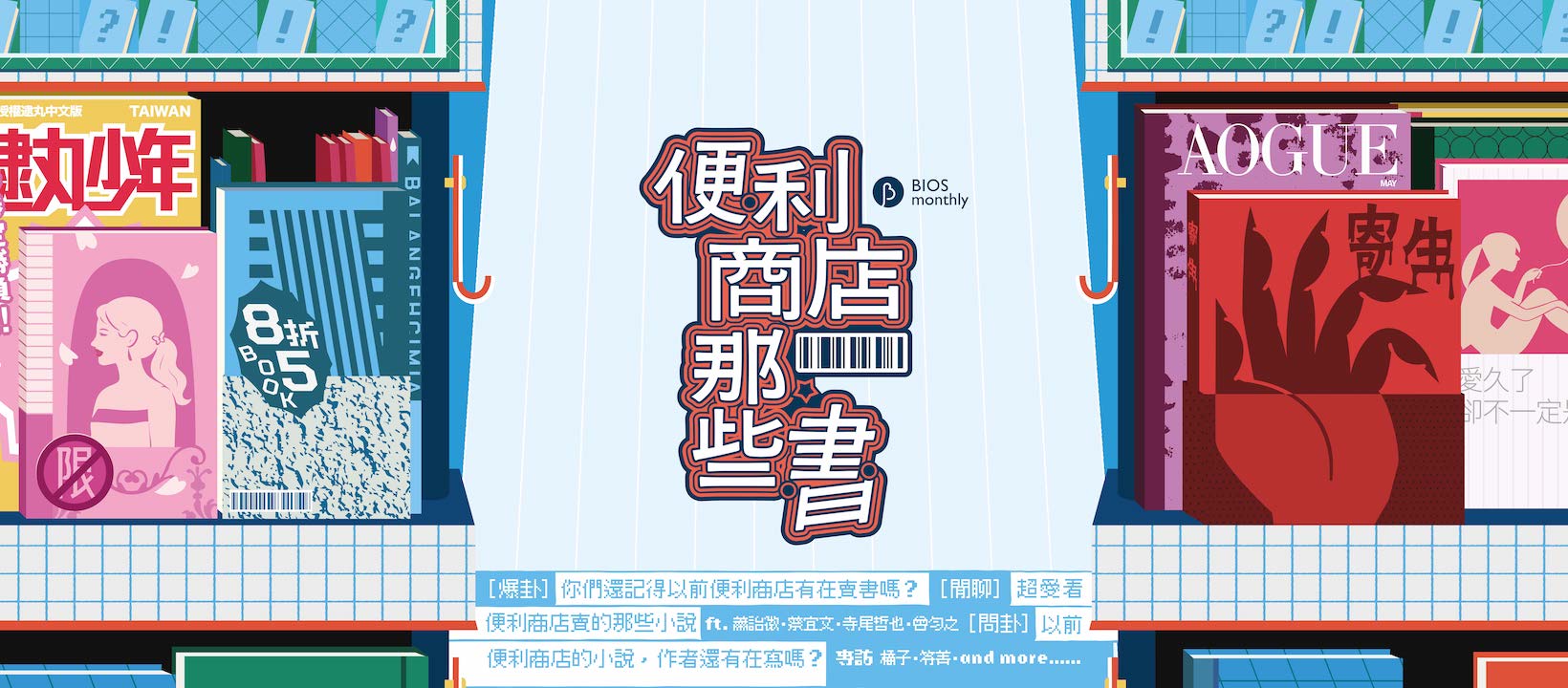
便利商店那些書
突然有一天想起,以前在便利商店買的那些書。
有幾本靈異小說後來成為你一輩子的陰影,霸總與嬌妻集合的言情小說現在想起來依然讓人雞皮疙瘩,但那是你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從書架裡挑出一本,結帳即走,那曾經那是我們最觸手可及的文學。



![[閒聊] 大家有在便利商店買過小說嗎? - 看板 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storage/upload/article/tw_article_coverphoto_20250515123328_qj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