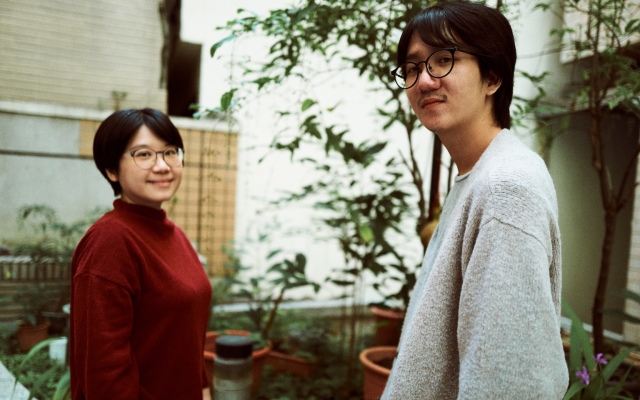獨特的光之氣味──專訪《共犯》導演張榮吉
在《共犯》的一開場,有個仰躺跌入水中的鏡頭,光線被水面雕琢成一片片、萬花筒似的,讓人想到真相也有好多面,像一個一個迷離的夢。在票房評價都告捷的《逆光飛翔》之後兩年,張榮吉帶來第二部劇情長片,從溫暖、輕緩、帶著希望的天平那一端,來到又酷又殘酷、冷冽而風格化的驚悚推理這一端。這樣的轉變讓人驚艷,也體現出和真實拉開距離、又同時深入內心崎嶇面的可能。不變的是,在那核心處所在乎的依然是孤單,是尋求溝通,和渴望陪伴。
專訪那天,阿吉導演酷酷地走進來,一身黑挺的襯衫,人高馬大又中長髮,但和他聊沒兩句話就會發現,那底下藏著靦腆,和細心回答每一題的誠懇。一開始,我們不免還是好奇:從紀錄片《序曲》、短片《天黑》到《逆光飛翔》,有七八年的時光都在和裕翔這位「被攝者」相處,一口氣跳到《共犯》,這當中有什麼心境的變化嗎?沒想到導演的回答是:「其實……沒有什麼心境變化(笑)!」
「我一直不覺得自己只能做某種類型,也一直想拍很酷、節奏很快的東西。當初遇到裕翔,以那時候擁有的資源,拍紀錄片是比較有把握的,拍《天黑》則是因為在拍《序曲》的過程中,我覺得最美好的一段卻沒辦法記錄下來(註 1),那段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就想用虛構的故事和角色去重現它。拍完之後,慢慢就喜歡上劇情片這個形式了。
後來拍完《逆光飛翔》,想嘗試不一樣的,剛好看到《共犯》的劇本,同樣以青春為題,卻是從一個死亡事件開始,而且是推理懸疑類型。它不只是個相對黑暗的故事,而是這些角色如何在孤寂的心境中掙扎,跟得到一些溫暖慰藉。剛好我自己也喜歡看推理懸疑,就想試試看。」
.jpg)
《共犯》劇照。
《共犯》的舞台設定在校園,片中孩子們在不同的校園角落相遇、互看,甚至是不同群體/階級之間折射閃滅的目光,十分突出。當被問及,是否對此特別有感覺?導演的回答也非常細緻:
「有感覺當然有,畢竟自己也經歷過。求學是個自我找尋的階段,因為不確定自己可以做什麼、想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而且同儕間一定有某種競爭的眼光,不管是念書或學技能,都會有這樣的人際壓力存在。」
由此連結,對於《共犯》讓人想起日本校園電影,像是《告白》的罪與罰的群體暴力,或《聽說桐島退社了》對小團體/階級排擠的描述,對此導演也表示認同:「最初看到劇本,不免會想到《告白》也是殘酷青春的主題,而且非常好看(笑)!當你聯想到,就會擔心會不會跟它相似。不過,王家衛導演跟我說:『別害怕你的東西跟人家一樣,因為一定會不一樣。』每個人的思維、每個導演的思維一定不同,何況是不同的國家。」他還提起另一件關於王家衛導演的往事:「他曾經對我說,你擅長拍『人之常情』。我那時候聽到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笑)。可是後來好好想過,我是拍紀錄片出身,紀錄片就是掌握角色的真實感受,可能是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或彼此經歷的共鳴。從《逆光飛翔》,我就一直在尋找跟觀眾的共鳴,或彼此能夠理解的價值,或大家都有過的生活感受。這好像就可以解釋為『人之常情』吧!」
.jpg)
《共犯》劇照。
接著我們聊到了技術面,一直以來,張榮吉是個非常注重美感的導演,《共犯》的視覺風格,那校園的光暈、水面的波紋,迷人又舒服,大量的逆光更彷彿某種註冊商標。這是不是刻意的選擇呢?
「陽光的感覺、光線的感覺是刻意的,而且我要最美好的光線都留在最後,就算前面有陽光也都是比較悶的。這用意是,故事裡的孤獨心靈都在尋找溫暖,而我希望每件事都有它的過程,你在這過程裡也許不一定得到答案,但至少有個呼吸的出口,或喘息的方式。我希望那是留到最後,伴隨著最金黃耀眼的陽光才出現。
至於逆光,它和《逆光飛翔》的逆光又不一樣,後者我追求的是光線感,但《共犯》的逆光是『剪影』。亦即,當你在很明亮的光線中,你可以看清楚每一張臉,看清楚每個人的不同,可是如果都是剪影,就變成一個群體,像阿兵哥剃光頭排排站那樣,都是一體的,沒有階級的分別。《共犯》就是大家都是同夥,所以我讓它是剪影的狀態,沒有彼此之分。」
他更進一步從色彩的角度作出比較:「《逆光飛翔》的畫面調性比較輕,比較清透,《共犯》則是反差大、色彩濃郁。而色彩本身也有區隔:校園內,比較有束縛或規範,色彩就少一點,校園外的色彩就多一些,像是小喬的房間,或街道上。後門和秘密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秘密湖是比較神祕的,所以讓綠意的感覺特別明顯,這綠意又其實蔓延在校園裡,所以我們拍走廊,都特意挑選有很多樹的,不希望乾乾淨淨,而是帶著綠色的神祕感。」
再說到《共犯》的聲音設計非常細膩,導演更是解釋得津津有味:「懸疑片的聲音很重要,它必須要跳脫寫實,如果你會疑神疑鬼,那是因為你有些其他的想像,你會擔心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那些擔心又引發一連串過多的聯想。所以我需要多一點『虛』的音色去製造氛圍,要多一點角色想像,才能引導觀眾的想像。但又不能太直接,不能像『碰!』『ㄥ~~』或鬼的聲音那樣,很容易變成鬼片的氣質。我還放了很多耳鳴的聲音,類似像溺水、或被重擊之後耳朵會有某種壓力,會有高頻的聲響那樣。」
.jpg)
回頭說說故事面,在導演的作品中,常可以看到年輕的角色、被社會視為還沒有「長大」的,其實也有艱困的人際要面對,甚至是某種孤獨。對此,導演以自己的經驗為例:
「當初看到這些孤寂,會聯想到自己的求學過程,高中五專都沒考上,後來去考了一個畫畫的學校,這時候就會有旁人眼光的壓力。可是你明明去那個學校就很快樂,甚至找到了自己要什麼。不過在那階段,相對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多支持,就會有一點孤單的感覺。
而在 casting 的過程中,剛好來參加的多數都是單親的孩子,他們每個都有自己不同的心理壓力和狀態,那幾天就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怎麼了?怎麼都有那麼多不同的困難?這時候你就像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就像被攝者,會毫不設防地講他們自己的故事,你就會覺得哇噢,很像裡頭的角色跳在你面前,你真的能夠理解了。就會更想好好呈現他們心裡的感受。」
然即使拿掉校園的框架,《共犯》的內涵其實是很社會面的,以一段段解謎和翻轉(twist)去辯證謊言與真相、怪罪和緝凶等等元素。我們忍不住問導演:選擇這題材,和台灣的社會現況有關嗎?
「其實很多事情它都有兩面,表象的跟真實的,有時候我們用既定的刻板印象,只能看到表象,但那不盡然是真實。這樣的兩面,也可以是角色的樣子:他可能是個被貼標籤的壞學生,卻實際上不是如此。他也可能是個好學生,但遇到無法解決的事情,選擇逃避的他又會有另外一面產生。
至於社會狀態的對應,無形之間一定有,《共犯》表面上是三個高中男生一起做壞事,其實探究到問題的根源,卻是旁人的漠視和不關心。所以旁人才是最大的共犯,或『漠視』才是最大的共犯。很多社會問題其實都是這樣,所以這故事沒有要針對特定事件。但如果它讓你聯想到某件事,就表示你產生共鳴了,這共鳴可能來自同樣都是台灣人、都經歷過的事。」
.jpg)
《共犯》劇照。
我們接著問,從《逆光飛翔》到《共犯》這兩年,導演本身的創作資源,是不是也進化了呢?
p>「其實我一直在尋找比較新鮮的合作,《逆光》當時是一位法國攝影師,用不一樣的視野看台灣,《共犯》則是找了很資深的廣告攝影師,他沒有拍過電影可是很喜歡電影,可以跟你聊很多,而且總是對畫面有追求,卻不需要靠太多的技術環節,譬如太多燈光去營造。他可以控制現場的光線,太陽光或反差等等,就可以讓氛圍感很凸顯。
另外當然也有些固定班底,像是配樂溫子捷、剪接李念修。《逆光》的配樂和《共犯》很不一樣,前者很多古典樂器和溫暖的表現,後者則是電子和甚至後搖滾,破壞張力比較大的東西,或是比較虛的,沒有旋律的寫意的音樂。至於剪接,《共犯》相對是更俐落、更明快的。總之,看到他們成長真的很開心,因為你相信他們有這樣的彈性,他們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最後我們聊到台灣的產業環境,關於創作者們不免要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作選擇,導演也表示:「我希望我的電影可以跟觀眾溝通,所以不希望太有距離。我相信自己不是很藝術的導演,不過,所謂的藝術是指美學,是指思考,這是每個創作者都會獨有的一種特質,這東西是不變的。就好像李安的作品,總會在商業市場有一定的價值,可是他的美學和思考也會有一定的份量,像是《少年 Pi》。你如果問我,比較期待靠向哪一邊?我只能說,我比較期待可以跟觀眾再拉近一點。」
當我們問,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個台灣前輩?導演謙遜地說,每個都很喜歡,都有不同長處。進一步追問他才說:「我很敬佩魏德聖導演的不服輸、勇於嘗試的精神。我也佩服侯孝賢導演的場面調度,要怎麼把畫面拍得那麼生活?那真的很不容易。那要靠真正專業的演員,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而且還知道鏡頭在哪裡!」
.jpg)
談到對未來的期望,導演也表示,希望環境可以更好一點,讓電影作為一個穩定的工作,它的經濟效益、工作環境是健康的,給藝術工作者的支持比重可以更均衡。那麼下一部片呢?他透露:「其實下一片已經在籌劃階段,劇本已經修到好幾稿了,是紀蔚然老師的小說《私家偵探》改編的。目前希望明年可以順利開拍,那將會是個成人世界的推理電影。」說這話的他臉上流露神祕,不難想像那又會是另一個全新的張榮吉。且讓我們期待從最溫暖的人情關懷,到最酷最跳躍的類型電影,都能被他獨特的光影氣質征服。
註 1:指的是導演和裕翔在海邊走路的段落,詳情請參考此文:〈誠懇而不浮誇──專訪《逆光飛翔》導演張榮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