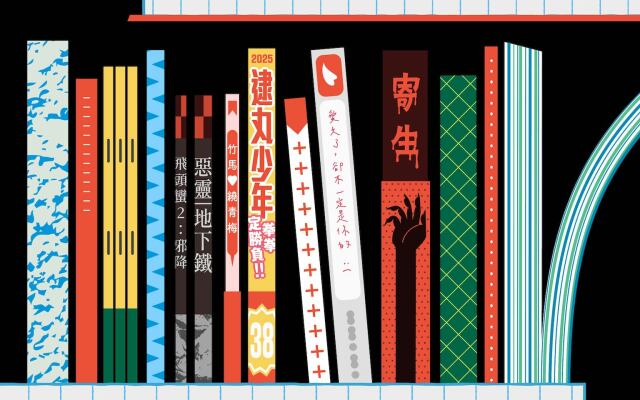《東京漂流》我心中的鋁棒
如果有人逼我拍出一張代表八〇年代的照片,我將拍下一柳展也砸爛父母頭顱用的那支金屬球棒。
而且我不會拍出陰暗模糊的刑事鑑識證物照,毋寧用類似精品雜誌《POPEYE》的手法,當成體育精品拍攝。其實我更想把一柳展也使用的鋁棒,拍成八〇年代的神像。
鋁棒、網球拍或慢跑鞋之類的體育用品,是戰後日本人血汗與眼淚結晶而成的神像。即使在八〇年代還是年輕人夢寐以求的神器之一,網球拍之類的體育用品,在高度成長期前後於美智子皇太子妃與明仁皇太子(當時)在輕井澤行宮度假的陽光下閃爍以來,一直是鐵網外的日本老百姓望眼欲穿的貴族娛樂。我不清楚對昭和個位數世代來說,這樣的娛樂帶給他們多深的印象,但是自從皇太子夫婦的皇室休閒活動公諸於世之後,日本民眾便更加努力工作,以實現他們心理貴族般的理想。最後形成的是配備各式各樣神器,三房兩廳獨棟附庭院的房子,以及許多可以在周休二日與兩個孩子共享天倫的半調子貴族。這樣的美滿家庭生活下,子女們也能如願得到心愛的網球拍。
然而他們未曾料到,普通的體育用品有一天搖身一變,成為殺人凶器,並且不偏不倚地命中自己的頭頂。

戰後三十六年來精心描繪的人生藍圖,在一座屬於自己的小城堡中實現,又像牽牛花瓣上的朝露般消逝無蹤。這起事件描繪出了八〇年代日本家庭的群像,並且被遺忘在戰後日本的歷史圖表中。群像圖上的「家庭」開啟了許多鬼門關口,卻絲毫不見「神」的蹤影。戰後的「住家」失去了神龕佛壇,由屋內一角的球棒或網球拍取而代之。所以我才想把一根球棒當做八〇年代日本家庭的魔像拍攝。
但是,這個企圖並無法實現。當然不會有任何如假包換的愛國者,會允許我在攝影棚內,一邊播放死者一柳幹夫(享年四十六歲)生前愛聽的〈我心悲戚〉,一邊拍攝擺在藍天大海背景圖前的凶器。即使找遍現在的國家警察體系,也極難找到這樣的人物。
於是我將視線從一支金屬球棒移到「凶宅」。再神通廣大的國家警察,恐怕也無法誇張地把一整棟「凶宅」當成一個證物扣押,並企圖在大眾面前隱藏這個事實。一座象徵八〇年代的巨大紀念碑,應該還留在川崎市高津區宮前平二丁目二番地三十號。
於是我在一個晴朗到沒有一片雲、沒有死亡的陰影,健康而清潔又充滿進步、豐饒、安定與調和,最能烘托日本家庭與人們笑容的好日子,出發前往一柳家的「住處」。
在沖繩縣形成的二十二號強烈颱風邊緣掃過關東地方後的隔天,也就是十月二日(昭和五十六〔一九八一〕年)的天空,一如預期帶來一片秋高氣爽,算是老天爺奉送的紀念照拍攝良機。我扛著那位攝影界大老拍攝奈良大和路時也用過的 Linhof Super Technika 四乘五相機,以及 Gitzo 製的 RNO-4 三腳架,往川崎大和路走去。
我從國鐵田町站坐到大井町,在轉搭東急電車月台邊一家叫做「田園蕎麥麵」的立食小店點了一碗一百五十日圓的清湯烏龍麵吃,吃完以後 便上車坐到二子玉川,再轉搭田園都市線到宮前平。
沿路我看著窗外的景色。
這條田園都市線,果然是蓋在田園都市上。東急列車開過了多摩川,窗外的景色就如同田園與都市的協奏曲一般。
透過都市的貫通,鄉下的農家也變成了田園,並陸續興建了具文化進步性的住宅,最後變成了田園都市。變成了田園都市之後,農家變成一種文化,在昭和五十一年春,一柳宅落成當時的地價大約每三點三平方公尺二十八萬日圓,到了命案發生四年後,已經超過一百萬日圓,創下上漲率全國第一的紀錄。
田園都市線穿過了綿延不絕、寸土寸金的大地。秋天舒適的陽光透過門窗,照進綠蔭中每一棟充滿文化氣息住宅內,一棟一棟從我面前消逝,而我似乎可以聽到一首愛與恨的抒情歌。在我的聯想世界中,窗外的每一戶人家的角落,都隱約帶著一股鋁棒發出充滿愛恨的啞光。
我心想,這真是一片充滿詩意的風景。到目前為止,我從未對這些塑膠感十足且枯燥無味的日本建築文化有過任何印象,但是這次我看到的風景,其實饒富詩意。一九八〇年發生的鋁棒殺人案,可以說是區分日本人風景觀的一大分水嶺。
案發後的風景,帶有一種嶄新的日式無常觀。我看著窗外的那種風景,不禁想起一段詩吟。
川流不息兮,河水已非源之水。浮於死水之上,水泡時生時滅,永無常住之理。世上眾人偕其屋宇,亦復如是……
與丈夫一同慘死在寶貝兒子鋁棒下的一柳千惠子夫人,在死前的三個月有感於夫妻關係的漸行漸遠,在日記中引用了一段《方丈記》中的句子,並以此感嘆人世間的無常。
但是她的丈夫幹夫,卻一直唱著〈我心悲戚〉:
——大海分開我和你 不顧我如此愛著你
無情客船出港邊 卡斯馬卜給,卡斯馬卜給……
電車的車窗上貼著印有「珍惜心靈溝通——日產生命」文案的人壽廣告。我隔著車窗,看著窗外田園都市虛幻的景色,陷入一陣沉思。想以詠歌回應千惠子夫人的這段詠歌,於是以近似剽竊的風格寫成一闕:
四濺血花 更易流進 最上川
所謂「更易流進最上川」,可以形容日本這條河流速度更為湍急的樣態。沿著流域往上追溯到八○年代的水源,可以發現到從新宿西口巴士縱火事件、靜岡瓦斯氣爆事件、一柳展也的犯案現場飛散出來的血海,並與深川商店街噴出的血漿匯流,在時間的流域上不斷蜿蜒前進。
中午十二點半,我踏上宮前平站的月台。
天空中央偏西的太陽,照耀著山邊的新興住宅,窗戶的反光格外刺眼。這些住家歌頌的光明,在這片永遠安詳的家園,合唱出過於聒噪的讚美詩。
……穗積診所‧神經科‧內科、河上外科、河田牙科、川本內科、砂田婦產科、櫻井接骨院、森本牙科……。
其實這一帶也有很多小診所。
遠方一角隱約可見一柳宅的黃綠色屋頂。
當我穿過車站站內光亮如新的文教堂書店時,朝著宮前平店的暢銷排行榜瞄了一眼。
第一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第二名《雜學趣味讀本》第三名《會罵孩子的父母與不會罵孩子的父母》第四名《窗邊的小荳荳》第五名《小說電通》第六名《堤義明偉大點子的秘密》第七名《捲土重來》第八名《真幻魔大戰》第九名《翻車魚雜學記》第十名《情色街道》
我在路上明白了這一帶是由八成抱有主管野心、閒暇雜學與一點好色的男人,以及兩成為了養育子女鎮日苦悶的主婦所構成。不一會兒我便抵達了一柳宅的圍牆外。
我跨過石牆,已犯下不法侵入的我,先在院子裡小逛一陣。
……棕櫚竹的影子、椎栗樹的枝葉、杉樹的香氣、竹葉的搖曳、芒草間的反光、玫瑰的刺、杜鵑花的樹梢、松葉的垂簾、蘗花的火星、山茶花的小舟、茅草的刀鋒。
被野放在都市四季中的植物,再度回到野生的樣貌,小蜘蛛留下的蛛網在枝幹間不斷照射反光。一朵白色的玫瑰,背著太陽逐漸枯萎,土中傳來的荒草味,更增添了庭院的荒蕪感。
在雜草修羅道的另一邊,有一棟門戶封閉的宅邸。
房子的背後是一片藍天。
一柳宅的遮雨拉門已經完全封鎖,幹夫生前的臥室也被拆除。在秋天午後的艷陽下,這棟門戶密閉的住家燦爛地閃爍,看起來更像一座祭壇。
.jpg)
住人與棲所間之無常爭奪,無異牽牛瓣上露。
朝露有時落,唯花留存。
花且苟開,日照則枯。
時有花蕾與露同滅。
此時不滅,亦無待夕暮時。
(《方丈記》)
我撥開蜘蛛絲、踢開雜草,在地上豎起腳架,裝上四乘五相機。這棟「住家」在對焦玻璃上上下顛倒。景框底下的「藍天」,更使人突然聯想起一個「家庭」一夕間墮入地獄深淵的意象。
我拍了幾張照片,才準備離開時,踩到一個可憐的小東西。
……是杜鵑草。
一叢杜鵑草,就在這塊庭院的隱密角落兀自開著花。
我看到這朵被草掩蓋的花,不知何故感到一股小小的衝擊,甚至感受到靈魂的最後一絲殘影。如果一戶人家的庭院象徵的是家庭主婦的心理,這幾朵小指尖大小的淡紫色小花,對千惠子夫人來說又是什麼呢?……
於是我又想起了她在日記中的一段話。
雖然痛苦,雖然寂寞,
仇,
恨,
憤怒,
絕望隨著淚水留下來……
上面是否開著高潔的花朵?
(千惠子夫人日記)
杜鵑草開出的花,就如同千惠子夫人日記中的文字一般薄倖,楚楚可憐中也帶著一種純潔。
我又想起《方丈記》中對於杜鵑(鳥)的一段描述:
(夏)聞杜鵑啼。
杜鵑啼聲,
連向死之山路。
杜鵑草是秋天才會開的花。
在千惠子夫人喪命的十一月尾聲,杜鵑草的花瓣也正飄零。
圖文資料:臉譜出版 《新版東京漂流》

作者:藤原新也 SHINYA FUJIWARA
出版:臉譜出版




![[閒聊] 大家有在便利商店買過小說嗎? - 看板 BIOS monthly](https://www.biosmonthly.com/storage/upload/article/tw_article_coverphoto_20250515123328_qj2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