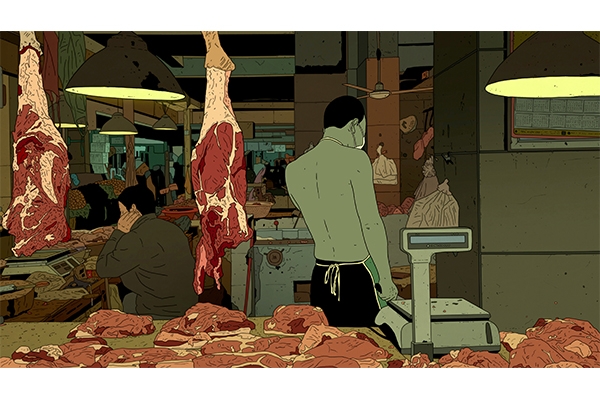拍電影,哪來的勇氣?專訪 2017 柏林新銳營學員廖克發導演
邁入第 15 年的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於知名劇場空間 HAU Hebbel am Ufer 展開為期六天的活動。2017 年新銳營的主題是「萬夫莫敵的勇氣」(Courage Against All Odds)。走在柏林街頭,即可以看見「沒有人會投資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找不到任何觀眾群」、「為什麼不找份正經的工作?」等斗大字樣的海報文宣。單刀直入的標語,反向質疑你的拍片夢想,將影視製作會遇到的困難條列出來,目的即希望能藉由此活動,理性地剔除創作者製作過程遇到的障礙。

柏林新銳營內容豐富,除了融合「快速約會」概念的人際連結(network)活動、畢業學員的最新作品放映、製作環節專門課程,如藝評寫作;以及契合當下趨勢的專題討論,如群眾募資、VR 技術等。系列活動還包括「企劃工作坊」 (Project Lab)——由 40 位學員帶著製作中的作品,分別參與三種類別 ( 紀錄、短片、劇本發展)的工作坊。經驗豐富的導師與提案講師,五天內一起密集地檢視各計畫內容。各工作坊最後皆有成果發表,讓學員向來自各方的製作人、募資者、發行商等介紹自己的作品。
這次 250 位學員分別來自 71 個國家,其中包括 106 位導演、49 位製片、15 位演員、5 位編劇、17 位攝影、14 位剪接、13 位場景設計、6 位配樂、8 位聲音設計等幕後專業,以及 8 位影評、與 10 位發行者。在台灣求學、拍片的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為代表台灣唯一入選學員。剛抵達柏林、一下飛機即收到《不即不離》被馬來西亞政府禁演的消息,原本即將於家鄉上映的新作,卻因為電檢聲稱影片內容「與馬來西亞共產黨歷史事實不符合」,無法於大銀幕上播映。風塵僕僕前往市區準備參加柏林影展新銳營的他,腦中思索著因應對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似乎正悄悄呼應了此趟柏林新銳營強調電影拍攝現實面的主題。
新銳營結束後,導演回台與我們暢所欲言地分享此次柏林之行的想法與體悟,同時也談到了籌備中的電影與創作遇到的課題。
Q:當初為什麼想參加柏林新銳營?申請條件是?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製片陳璽文(Stefano Centini)希望我去參加,另一個原因是我 2015 年參加東京新銳營(Tokyo Talents,東京 FILMeX 影展底下活動之一,與柏林影展聯合舉辦),其中一位指導老師 ChristineTröstrum 也是柏林新銳營的招募團隊,當時她就極力推薦我申請。
申請時需要繳交一個五分鐘的作品集錄,我剪了《妮雅的門》與《不即不離》進去。Christine 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為《不即不離》,她一直追蹤我這部紀錄片還有《菠蘿蜜的愛》(註 1)的進度。那時候去東京新銳營的提案即是用這個故事,因此她才建議我申請今年的柏林新銳營。
|
廖克發導演提供。 |
Q: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有哪些?
因為想要多瞭解演員指導的部分,我有去聽演員課 “Meet the Expert: Casting”。另外也去聽了關於新興傳媒創投的專題討論 “Meet the Business Innovators”,探討如何建立新的平台、讓電影銷售變得更簡單。另外,我對正在發展的題材有興趣,像是 VR。
我還去聽了企劃工作坊紀錄片組的成果發表(Project Labs Presentations: Doc Station)。Doc Station 選入十部正在發展中的紀錄長片,今年入選作品來自菲律賓、巴勒斯坦、加拿大、古巴、葡萄牙、哥斯大黎加、瑞典、波蘭、德國等九個國家。活動進行方式,是由一個主持人向各企劃案的導演輪流提問、引導他們講話。這種形式的好處,是大家不需侷限於導演本身的演講能力來了解這個企劃,因為他們未必有好的提案能力或穩健的台風,但有好的案子。主持人同時也是他們的導師,非常清楚他們的企劃內容,因此可以幫他們補充。
|
@Peter Himsel, Berlinale 2017 |
Q:會與課堂夥伴討論彼此的創作嗎?
去新銳營認識學員就跟平常交朋友一樣。參加者有發行商、導演、製片、音效師、演員等不同身份。如果你是發行商或製片,認識越多人越好;但作為一個導演,我不用認識這麼多人,我寧願認識得深而不是認識得多。聊得來,你會感受對方想聊,還是只是想要交換名片。
這次我沒有認識很多人,只有一位印度導演和一位義大利導演。後者前一部作品入圍威尼斯影展,是關於更生人出獄後不被社會接受的劇情片。拍之前的田調做了很久,後來演那個角色的,就是現實生活裡的那個人。虛實交錯,我很喜歡這樣的手法。也因為這部片,後來他在義大利變成知名人物。我覺得電影這一點特別好玩,可以改變某個人的一生。當全國都對他有所期待,你是用電影在改變這個人。這位義大利導演說會寄他的片子給我看;他也想看我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對我神秘的祖父很好奇。
在那邊會被安排與其他學員同住,我的室友是一部新加坡電影《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的混音師 Nikola。他是西伯利亞人,那部影片在曼谷調光、剪接,混音在新加坡,拍攝在泰國,算新加坡電影,拿新加坡官方文化補助拍攝的。新加坡的補助沒有要求一定要在新加坡拍,只要求主創(導演、製片)是新加坡人即可,台灣還無法做到這樣的程度。Nikola 很興奮地跟我分享他如何後製大象的各種聲響,他說所有的聲音都是做出來的。他花很多時間揣摩大象要怎麼樣有情緒、如何讓畫面中的大象發出各式情緒的聲音?
Q:導演也曾經參與過其他的工作坊,柏林新銳營有何特別之處?
東京將重點放在提案訓練,相較之下,柏林就比較專注在 networking (拓展人脈)。柏林有很多社交機會的活動設計,像是 Turn Table,也就是快速約會的晚餐,可以在短時間認識非常多人。活動細節都很用心,用顏色來分別學員與導師,然後平均分配導師與學員。每上一道菜,學員就會跟隨新的一位業內專家,或許是製片、也或許是國際片商。像我就因此而分別與柏林影展選片人、歌德學院的代表、製片 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 等專家認識(其中,我和製片 Raymond 本來就認識)。
柏林學員是 250 人,東京是 15 到 18 人,柏林的規模相對大很多。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是 task-oriented(任務導向)的,和東京新銳營比較接近,著重在技術訓練和企劃案內容的幫助上。
Q:此次柏林新銳營有一專題講座,將製片人 Raymond Phathanavirangoon 主導的跨國合製電影《行徒》(The Apprentice) (註 2)作為案例深度剖析,請問導演對 co-production(跨國合製)的看法如何?
歐洲學生很習慣跨國合製,他們從學生時期或畢業製作就開始這樣做。歐洲學校本身國際學生就多,在德國唸電影的,可能有從波蘭、中東等不同地方來的學生,因此他們很習慣要去另一個國家拍攝,或是不同國籍學生在一起的環境。亞洲的話,或許新加坡、泰國近幾年比較普遍,但因為語言隔閡,台灣還是很少有這樣的模式。就我近來觀察,現在的跨國合製新加坡最多,也有越來越多歐洲的製片常駐在那裡。
但我也不知道跨國合製是好或不好。拿我的劇本來說好了,現在《菠蘿蜜的愛》進入第六稿了,一直在寫。目前正在申請的一項計畫,需要將此劇本翻譯成法文,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是,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哲學思辯的過程、希望看到你 philosophy(哲思)的 questioning(質問)在裡面。但那不是我們說故事的方式,我們不會說故事將它辯證。我們會做,但不是用一種外顯的衝突去做。跨國合製是不是好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哲辯一點還是少一點,我現在仍處於掙扎期。
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激盪過程
創作不是很清楚的時候,把自己擺到 250 個不同國家來的學員裡,很容易失去自我。你會想去符合大家的期待,感覺到其他人對你的預設立場:你應該要怎麼樣、亞洲人應該怎麼樣?你們國家應該很糟吧?人權不公吧?經過每次的交流、這些期待累積起來……從這麼大的地方、感受到這樣的氣氛再回來,很容易相信你自己就是那樣。
我碰到一個印度女導演 Natacha,她是拍同志議題的。她對印度文化、制度和電影都很有想法,也很清楚她參加的目的就是希望入選影展、拿資金;回去後也不要跟政府對著來,這樣才是比較聰明的。我覺得亞洲導演要知道這個,你自己要清楚你踩的步是什麼,不是一味出席這些活動。
我去看一部摩洛哥電影,我看十分鐘就覺得這是費里尼吧?鏡頭像費里尼、演員也像費里尼。我就跟另一個摩洛哥學員聊天,他問我覺得那部電影怎麼樣?我說根本是摩洛哥的費里尼,他就說,不這樣拍,電影出不來、也不會拿到資金。我問他摩洛哥電影到底長什麼樣子?肯定不是很費里尼的剪接。電影的敘事不只是追溯回電影工業,也關係到這個國家有沒有文學、講故事的方式是什麼?我期待的摩洛哥電影是更不一樣的東西,而不是費里尼。但那導演也是為了求生存,那這樣子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不知道能不能跳開這宿命?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就算有些導演是取巧,但重點是這些導演知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站穩了,再開始拍自己的東西。我認識一些中國導演,他們比我們自覺更強,他知道用這種方法,他知道他要什麼。那台灣創作者知不知道?
Q:承上述想法,或許文化性質較為接近的亞洲各國之間更適合跨國合製?
有時候是文化信心的問題。當你對自己的文化很有自信,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糾結。每次想到「跨國合製」,一定會跟歐洲牽上線,因為還是比較跟資金在流動,我覺得亞洲本身的 network 相對沒有那麼強,但有機會我也滿想去東南亞各國拍片,像是柬埔寨、越南等地。
Q:參與柏林新銳營有什麼樣的實質幫助?
雖不會馬上找到合作夥伴,但可以了解他們眼裡的亞洲到底是什麼樣子。飛到柏林才知道我的片子被禁,所以整趟下來很多時間在處理這件事情;要不要公佈被禁的消息、要不要辦線上首映等等。有時候政府是霸道的,你就要去對看他。如果我們說一個政府是壞的,他們認定那政府是不好的,彷彿變成反對他的所有東西都是好的,這樣是不對的。西方的整個文化有辯證 —— 一定要透過正反去辯證。我不覺得那是我們的文化。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有經歷過的是,二戰反左浪潮下我們扶植了錯的右派政府。我們不去問右派對不對,我們都扶植很怪的政府,整個東南亞都很亂。但提到這就跟電影有點遠了。
|
廖克發導演提供。 |
Q:有什麼建議想給台灣的創作者?
我覺得我們還是在摸索的階段,因此很容易沒有信心。我見過一個日本導演,他的英文非常拙劣,但提案的呈現方式非常好;或者我與韓國創作者接觸,他們英語也不見得很好,但他們不覺得講英文是件丟臉的事,他們對自己的企劃(劇本)很有自信。這種自信不是「我是一個電影人」的驕傲,而是因為你很喜歡一樣東西,你很想要拍這個東西、很想要保護它的時候,那種驕傲很自然就會出來。這種愛,我在周圍比較少看到。
像是在東京新銳營,有位日本導演他用照片講話,每張相片只講兩句話,但你可以感受他很愛他拍的東西、他很有想法,你真的感覺得到。去感覺一個人愛不愛他拍的東西,有時候是不需要語言的。但這不代表柏林新銳營裡大家有做到這件事,也有人純粹是去拓展人脈、增加電話簿名單,我反而覺得那東西(追求上述的「愛」)比較重要。
就像那個摩洛哥導演,他也不知道摩洛哥電影長什麼樣子。在那種茫然裡,你不一定馬上能夠知道答案,但你不能把它放掉。拍片不能那麼安全,要實驗,不敢冒險拍電影就會很無聊,放掉那個東西就會變得很無聊。
採訪後記
身為一個柏林影展的觀眾,雖然我無法直接參與柏林新銳營,但透過導演的分享,能夠一窺柏林影展如何扮演一仲介與指引的角色,將欲投身、努力耕耘電影創作各個環節的專業人士,拉攏在一塊、撞擊出火花,並助他們一臂之力,達到作品質地的提升與創作者動能的產生。
經幾番的思量,導演後來決定在線上舉行《不即不離》的大馬地區首映,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六天的時間免費開放於網路上觀看,最後創下高達七萬人觀賞的紀錄。而他正在發展中的劇本《菠蘿蜜的愛》於三月底獲知入選坎城影展世界電影工廠——新導演工作坊,因此五月即將前往坎城,接受下一階段的劇本塑形洗禮。無論是下游的發行宣傳或是上源的劇本發展,當令人頭痛的考驗迎面而來,或許就該像克發導演,咬著牙突破重圍,往下一關前進。
讓我們一起期盼他下一部作品開花結實的時候。
延伸閱讀:廖克發X陳璽文|傳說中的國際資源,如何看得到更吃得到?(上)、(下)
註 1|《菠蘿蜜的愛》為廖克發導演正在發展的劇本,拍攝完成後即將成為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註 2|《行徒》( The Apprentice ) 為新加坡、法國、德國、香港、卡達等國合製的電影,獲頒 2016 金馬影展奈派克獎,並代表新加坡角逐 2016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影片。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