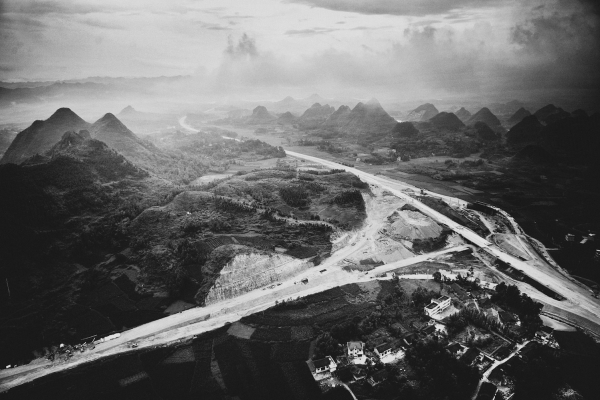明明放棄是那麼容易──專訪許雅婷《大風之島》:拍樂生,我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缺席
2006 年拍完畢業製作《樂生活》之後,許雅婷離開台灣,到美國芝加哥讀電影。那正是樂生療養院抗爭最嚴峻的時候。
嚴峻從 2007 年 11 月開始,台北縣政府正式在樂生療養院貼出拆除公告,並對院民祭出限期搬遷。此後院內建築一棟棟倒下,從大門到院舍。2008 年 12 月 3 日,上百名抗爭群眾聚集在貞德舍內靜坐抗議拆除,台北縣政府則出動五百名警力驅趕,最後一位院民藍彩雲堅守在貞德舍內,直到捷運局工人持電鋸破門,走出時掩面哭泣。
那些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她不在。
「我其實是在一個沒有好好告別的狀態離開。我那時候的確有罪惡感跟很複雜的情緒,有一種自己是逃犯的感覺。」
後來回到台灣,也回過幾次樂生探望院民、參加活動,卻不再拿著攝影機。許雅婷形容自己像是女兒回到娘家,身份與位置轉換,一下子找不到自己。「那些活動又讓我更痛、更無力了——明明他們的生命裡還是有好多課題要面對,可是我怎麼只能做一些很康樂的事情?」
於是也曾經轉換位置。2011 年,捷運局在新莊機廠邊坡開挖引發走山危機,許雅婷在前線的聲援隊伍裡吶喊、表演——單純,安全,不用擔負任何責任。「但就覺得好像這也不是我的位子。那不是我的能力能做到最好的事情。所以滿長一段時間,都會有一種力有未逮、好像有力量可是卻動不起來的無力感。」
.jpg)
直到 2016 年底,國發會通過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劃,樂青成員邀請許雅婷和當年合拍《樂生活》的夥伴林婉玉,回到園區拍攝重建 Y 字型入口的大平台方案推廣影片。「那時候一拍就覺得,哇,那個感覺都回來了。」
彼時距離 2006 年離開,已經過了 10 年——等到她把紀錄片《大風之島》完成,那又是 9 年之後的事了。
初入
2005 年 5 月的「音樂・生命・大樹下」音樂會,那是許雅婷和林婉玉第一次踏進樂生。那時候她們就已經帶著攝影機了。
起初只是想為畢業製作找題目,從 BBS 上知道了樂生療養院——倒不是被議題吸引,更接近一種純粹的好奇與驚異:「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一個社會議題,是距離我的家那麼近的。」
說近亦不算太近。捷運新莊線還沒蓋起來的年代,兩人從政大騎著摩托車到樂生,從城市的邊緣到另一個城市的邊緣,一個半小時的路程處處顛簸,最終來到的地方卻超乎想像:平房,山坡,年長的院民騎著代步車緩慢移動。許雅婷的第一印象是,回到了故鄉。
即使她一個台北都市小孩,根本從未擁有過那樣的故鄉。
如今點開網路,大有已經整理得清晰詳盡的議題始末與資訊:1994 年,因為捷運新莊線機廠的興建,捷運局與樂生院方確定「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方案,讓這群曾經因為國家暴力而被強制隔離於樂生的漢生病患者,又再度因為國家暴力而流離失所。而後青年樂生聯盟和樂生保留自救會相繼成立,抗爭從此浮上檯面。
答案寫在那裡,但她寧願自己去找。打從最初,她們就是透過攝影機認識樂生議題。在舊院區蹲點、也到新大樓聽聽不一樣的聲音,所有關於議題的辯證,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我覺得那個進入的方式有點像記者,其實現在想起來是很古典、但是又很紮實的方式。一般而言比較聰明的孩子可能就會直接去找自救會或是樂青,從那個地方進入議題是容易的,可是我們那時候選擇了一個好像比較困難的路,自己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樣貌是什麼、我到底想要記錄什麼?」
.jpg)
甚至連拍片這件事,都是樂生教會她們的。
樂生抗爭剛剛開始的那段日子,許多紀錄片導演或劇組紛紛進駐,而許雅婷和林婉玉當時還只是個修過紀錄片課、連拍攝技術都不算純熟的大學生。反倒是站在鏡頭之前的院民,已經習慣抗爭中各種攝影機包圍的日常,他們懂得拿捏與拍攝者的距離感,樂於甚至善於表演。
表演並不等於虛構,更像是一種運動中的必要手段。「有些時候會覺得他們知曉我們的鏡頭、想要利用我們的鏡頭說什麼,這個東西是存在的——但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透過這個鏡頭、這個表演,你到底想要跟觀眾說什麼?我覺得那個東西才是核心,而不是去在乎那個 moment 它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假的。」
而彼時初入議題,一切都仰賴受訪者的給予,前進沿途摸索,看到生病的身體就拍,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好在院民們習慣身處鏡頭之前,倒也沒有覺得不舒服。「因為當時去樂生療養院做學習的人很多,他們對學生這個形象相當習慣,所以我們的那個關係並不像是偷窺或者是剝削。」
多年之後剪接《大風之島》,重看看近二十年前的拍攝素材,許多隱藏在距離裡的訊息才終於被讀懂。但在那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中,一個紀錄片新手當下能夠抓住的,只有那裡的人。
.jpg)
有話想說
首先被她抓住的人之一,是《樂生活》裡作為主角的院民黃文章,招牌曲〈金包銀〉唱遍各種抗爭場合,一句自己改編的歌詞「人是好命囝/阮佇咧樂生院」,比任何運動口號都還響亮。
「其實滿多紀錄片的劇組進去,大致上都會圍繞著自救會跟跟文章伯,這樣子表演性質比較高、很容易被拍攝的人物。可是我看到的文章伯又是不一樣的人——那時候可以感覺到我跟他很不一樣,不管是外觀、年齡、性別,全部都非常不一樣,可是他很認真地要跟我溝通、想要我理解他的感受,任何問題他都很直率地回答我。」
許雅婷形容,那是一種課堂之外的衝擊,「就是他們真的好坦率哦。」不像許多紀錄片受訪者初面對鏡頭,往往先有戒心隔離,甚至禮貌客套底下都有戒備。「但文章伯不是,他那種距離感是很親切的。」

《大風之島》劇照。電影開頭,是樂生院民、自救會成員黃文章唱著自己改編歌詞的〈金包銀〉,那是他最代表的主題曲,歌詞也像在隱喻每位漢生病患者的生命。而二十年前許雅婷的短片《樂生活》,同樣是以黃文章唱著〈金包銀〉開場,既是致敬,也是呈現樂生療養院的變與不變——許雅婷說,「那是最迷人的。」

《大風之島》劇照,樂生保留自救會的榮譽會長李添培在遊行場上擁抱樂青成員。
《樂生活》的另一位院民主角黃金英,總是穿梭在院區裡照顧其他院民,外表又沒有漢生病常見的外顯病徵,看似與常人無異,甚至不會意識到她是病人。「可是她又在樂生療養院——那對我來講很迷人。」
迷人的是看見議題裡每一個人的複雜與立體,「大部份人都會覺得他們留在這邊不能出去,那他們一定是無法融入社會、有比較明顯的身體疾病。可是金英並沒有那些標籤,那到底什麼東西影響了她永遠住在這裡、讓她沒有辦法回去?」
在樂生,院民的多元性超出外人想像——漢生病固然是他們在這裡的最大原因,但不只病作用在軀體上有不同的程度,社會的各種面向也都是如此:有人結婚成家亦有人終生未婚、有人做粗工維生,也有院民早早在外面的世界投資買房。弱勢是常態也是動態。
甚至,連對議題的想法也不見得全然一致。
一開始許雅婷在面臨拆遷的舊院區和新落成的新院區大樓兩地穿梭,不乏許多已經搬遷到新大樓的院民告訴她,漢生病患者本來就是應該被拋棄的,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他們想要告訴我的故事是:我們身為一個弱勢的院民,政府對我們那麼好,我們就應該搬。」
同時另外一邊在反抗拆遷、爭取樂生療養院原地保留,兩種聲音也有在心裡打架的時候,「老實說很容易不小心被那種『社會發展多好、我們被犧牲是應該的』,這種大部份人的語言給說服。」
「可是反過來想,這些不願意屈服的人,他們背後是不是有更強大的理念、更強大的聲音,要去告訴這個世界?」

《大風之島》劇照,圖中為以故樂生院民湯祥明於抗爭現場的舊照片。

《大風之島》劇照。圖中為 92 歲的前任樂生自救會會長藍彩雲,藍彩雲於 21 歲進入樂生療養院治療,至今已經超過一甲子,電影記錄下當時藍彩雲被選舉為自救會會長、並且帶領院民與政府抗爭斡旋的畫面。
最後在《樂生活》或《大風之島》裡,她選擇沒有放進那些新院區院民的聲音,一方面是自覺有義務對受訪者負責,「如果我展現他們講的這句話,到底對於社會的意義是什麼?大家會不會用一種比較平庸、保守的價值觀看他們?」
況且,「今天一個過得很好的人,他其實不需要發聲。當一個不需要發聲的人,你把鏡頭給他,對他來講是一種困擾。」
訪與不訪,放與不放,那其實是對紀錄片本身的反覆辯證。拍片的人與被攝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建立在創作者個人的創作慾望,「對我來說,有話要說是重要的。即使現在做作品,我都會第一個問我自己:這個受訪者有沒有需要一個紀錄片?他有沒有話要講?」
「我的經驗是,很多被記錄的人是不得不來到這裡被呈現的——我不是演員,只是一般人,你來到我的生命中其實是會干擾的。所以對我來講,受訪者他必得要經歷過很大很大的自我成長跟自我抗爭,他才會成為一個紀錄片的受訪者。」
幫他們把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就是她心中紀錄片的意義。
你有什麼特別的
然而 2016 年回到樂生拍攝,許雅婷一開始也沒有做紀錄片的計劃——有話要說這件事,在當時的樂生議題反倒曖昧了起來。
經過 2000 年代最風起雲湧的抗爭階段,運動在 2016 年的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劃通過之後,反而變得疲軟,樂生看似獲得保留,許多不明白運動訴求的人會問:為什麼還要抗爭?
作為身在其中的人,許雅婷當然知道為什麼。有太多太多荒謬之事還在持續發生:對院民缺乏尊重的拆遷行動、重要會議中有意無意對院民的排擠甚至欺騙、欠缺整體規劃的新院舍、原始的 Y 字型入口意象被扭曲改造,入口延伸的無頭斷橋突兀地站立在捷運新莊機廠的大門口旁,不時有不明所以的人在社群上發問:這是什麼?
整個樂生議題還有好多話要說——但許雅婷自己卻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沒有拍攝計劃,第一件要正視的事情是:「我為什麼回來?」
還沒想清楚的時候,就先拍。「大概有兩年的時間不太知道自己在幹嘛,但我就是保持著每個月、每兩個禮拜回來。有時候拍運動、或是比較政治的東西,有時候又會回來拍一下生活。那時候拍了大量生活,就是要找回來自己拍攝的感覺。」
也不是沒想過放棄。「老實說,好不容易回去了,其實放棄是更容易的。」何況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你只要決定放棄就放棄了。有一天你不去,你就放棄了。」
後來許雅婷逼著自己買了一台專業的 FS7 攝影機,想說花了錢就不會放棄了,然後發現,自己一個人拍反而要比想像得更加輕鬆。
.jpg)
然而規律地長時間拍攝,看似沒有放棄,卻也沒有前進。
「其實有一段時間,阿公阿媽跟學生都沒有問我、沒有期待我要完成一個作品,那時候覺得無比地自由。但是又覺得,身為一個創作者不能永遠逃避,因為你會知道說有一個案子,你也知道一直逃避、一直拖下去會是什麼樣子。所以那時候我覺得好像我準備好了,重啟也拍了兩三年,應該是可以提案了。」
以為已經準備好,提案卻像是把自己打回原形。評審的第一個靈魂拷問是:拍攝樂生,你有什麼特別的?
「我那時候為了要證明我自己是最對的人,就進入到——我待在這邊那麼久、他們在我面前表現得非常得自然——的這個走向。當然這個東西是真的,但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其實真的要證明的並不是我跟他們有多特別,而是我對於這個故事的清楚程度。」
於是她才意識到,提案評審的問題背後,其實是大眾對於樂生議題的視角濃縮,「樂生議題其實有非常多先入為主的難題。它在新聞媒體上太多曝光,大家對於這個議題很累了、很多人都會說這個議題不是結束了嗎?可是那個結束,到底怎麼發生的?」
「我後來想想,那時候是我還沒有準備好要怎麼樣呈現現在的樂生,我才可以好好地告訴別人說,你說的是錯的、其實你根本不應該拿同樣的量尺來看我的故事。」
責任的長度
於是是時候,她該拿起自己的量尺。
二十年前拍《樂生活》,短短 30 分鐘的短片篇幅,以兩位院民主角為主體,再從人物帶到議題與抗爭。許雅婷形容那是很古典的起承轉合結構,很典型的學生片。
「老實說古典結構非常地 work,而且到現在看《樂生活》,我還是覺得是一個滿好看的片子。」
但古典背後,她知道其實是自己能力的不足——尤其是面對議題的不足。「我明明知道樂生議題下面有一個好深好深的海跟鴻溝需要被梳理,可是我沒有能力。我連那時候的政治現實我都搞不太清楚,就是在迷霧之中,我沒有辦法梳理得清楚。」
2020 年獲得文化部的資金後,《大風之島》開始正式啟動,許雅婷第一件做的事不是繼續拍攝,而是找來一位剪輯助理,整理將近二十年裡累積的所有拍攝素材,有三、四個月的時間裡每天什麼都不做,就是專心看帶子、做場記,然後再用極為傳統手工的方式,把所有的內容轉成逐字稿。
是在那些文字和影像的梳理中,《大風之島》才慢慢浮現。
「其實你在拍攝的時候,是無法看到那個全景的。因為你的視角就是跟著院民走、跟著這個運動的脈絡走。所以唯有透過素材的整理,你才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跳脫,好像全局地看到這件事。如果是拍攝,你永遠就是在這個角度,那你看素材的時候,你的距離也可以遠一點點。」
第一次的影片初剪。許雅婷記得很清楚—— 7 小時 48 分 31 秒。那是她整個二十年與樂生同步的生命史。
然後從七小時縮減到四小時,把大架構的場次拿掉,再慢慢修剪零碎的枝節,「到了三個小時之後,開始決定故事的主要架構。那時候就是難的了,因為你開始要面對你的影片要關於什麼、它是多大的一個故事。」
關於影片全景的藍圖,是在那時候才能真正看見:「原來我其實在記錄一個樂生園區建成,卻把這些院民的聲音、他們的存在給抹除的一個過程。」
而剪接到了這個階段,每一步細微的修整都重於泰山。許雅婷說,那是身為一個拍攝者、身為一個導演,對於素材的負責任。
「因為你的素材不只是服務你的訊息,其實你的素材也會影響他人的生命,跟別人看待他的方式。你跟你的受訪者很有信任,他願意展現所有的他給你,不代表你可以展現所有的他給觀眾。然後你要展現的東西背後,其實也反映了你自己對於他的理解、對世界跟對創作的理解。所以有一絲一絲不確定的時候,那個東西都會被觀眾看到的。」
.jpg)
.jpg)
那樣的堅定必得經過無數次自我的淘洗與錘鍊,「我決定的視角、決定揭露的東西,是不是都可以跨越時間的考驗,還能堅持著這些詮釋是對的?就算是揭露了強權,還是可以在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後證明那是經得起時間考驗——那個決定,我覺得是負責任的決定。」
「它背後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也就是你如何長久地看待這個片子。」尤其在剪輯的過程裡,魔鬼不時埋伏出沒:「譬如說你這樣剪外國人看不懂、你要不要更接近國際影展觀眾?你這樣剪是不是不夠有戲劇張力、是不是不有趣?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會在你的心中,不停地考驗你的每一個決定。」
她始終記得剪輯夥伴,來自日本的剪接師秦岳志教會她的:「這個負責任,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你。所有的界限跟尺度,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在這裡
畢竟這不只是關於樂生的故事,也是關於許雅婷自己的故事。拍了樂生二十年,這裡早就是她生命無法割除的一部份。
幾次國際提案的時候,她感受到有些外國影人期待她在影片中放入更多自己。也曾經拿著攝影機,在爬山過程中拍自己的影子,「拍過一次就覺得,好做作喔!在幹嘛!」
想起早年在樂生,許多熟悉的阿公阿媽習慣喊她「政大的學生」,「我不太喜歡這樣,有一陣子覺得那樣的狀況不太對。」於是有時候她會刻意不帶攝影機進院區,純粹聊天,或是在會議現場解說、翻譯,在不同的身份與位置上探索新的關係的可能。
因為她始終相信,樂生不只屬於自己。「樂生議題是個公眾而且巨大的議題,它不是個人故事,它是好多人的共同的故事,所以它必得承戴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重量。」
「當然我曾經有想過,是不是要用個人的立場來進入,因為的確在這個主流世界裡面來講,越難的議題用越個人的方式進去就會比較容易。可是我覺得那就又把這個議題侷限了——我回去又不是因為我有創作慾望所以回去,我回去也是不得不回去的啊!」
然而越到後面,自己的位置又再一次被重整安放。這一次,是因為院民們需要她的存在。
.jpg)
《大風之島》後段,黃文章逐漸失智,從原本的侃侃而談到需要別人引導對話,許雅婷的聲音開始頻繁地出現在紀錄片中。在黃文章說自己一生就這樣完蛋時,她告訴他,「你讓我的人生不一樣了。」而在黃金英遭遇迫遷低落沮喪時,她從遠處對她喊,「不要在乎別人!」
因為那些現場,她沒辦法不出聲。「文章伯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到處走,你只能坐在那邊跟他對話、跟著他一起面對他人生的窘境,而我永遠會相信他們的身體跟他們的窘境是公共性的。所以那時候我就想透過各式各樣的聊天陪伴他,記得他曾經發生的事情。」
「那金英阿姨是因為我跟她是最親近的人,對於金英來說,我是在迫遷暴力中那一個信任的存在。所以於情於理,我都沒有辦法讓我自己做一個超然的紀錄片工作者。因為你知道她是誰,你就是有那樣子時間的厚度,你就是會被牽動進去。那些東西都是身為一個長久陪伴者,很自然而然的反應。」
而在影片裡保留,也是因為那份情感的絕對真實,毫無做作。「尤其在故事的後段,我們知道那個東西是重要的、而且它是這個影片裡面很珍貴的鑽石,所以我們那時候花了滿多時間在鋪排它,怎麼讓這個細節不會煽情、又可以去前後呼應。」
那是用二十年的生命沉澱出的情感重量。許雅婷不只一次在訪問裡說過,樂生形塑了她的世界觀。
「在樂生之後,其實我有機會接觸像廢死議題,但我一直都沒有辦法拿出攝影機。我可以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並不是所有的弱勢或是所有的社會議題,我都會完全一樣地關心。有些人可能會從樂生議題走到了土地議題或什麼的,可是我好像不是這種人。其實樂生議題對我來講,就是那一個議題而已。」
運動中也不是沒有傷害,蹲點那麼久,各種形式的暴力她都見證過——黃金英被迫遷那天,警察來到現場,她無法控制自己不害怕,「可是你知道,那天我還可以回家、我受傷了可以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或是找別人聊天,可是金英阿姨她就要過著那個已經被影響的生命,我到底憑什麼害怕?我們有什麼悲觀的權利?」
.jpg)
那麼多年裡,鏡頭裡的人也曾經悲觀,尤其隨著年紀衰老、病體不斷被截去,能使上的力道越來越小。同時運動似乎也在凋敝,每一次的抗爭集結,重複的場景,人數卻越來越少。2020 年,樂青成員再次發起六步一跪的抗爭苦行,從療養院山頂的靈骨塔出發,沿途跪行至衛福部。那天白天高溫 38.9 度。
而當年六步一跪浩浩蕩蕩的上百人,如今只剩寥寥可數。
但院民們始終都在。離不開也好、決心奮鬥到死亡也罷,他們都還在那裡。
所以她也在。「我們就是只能走下去。」
《大風之島》紀錄片上映發行經費集資計劃
集資頁面連結|https://wabay.tw/ref/6Ws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