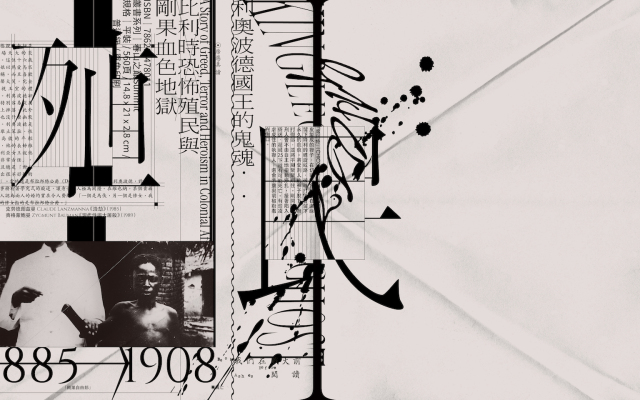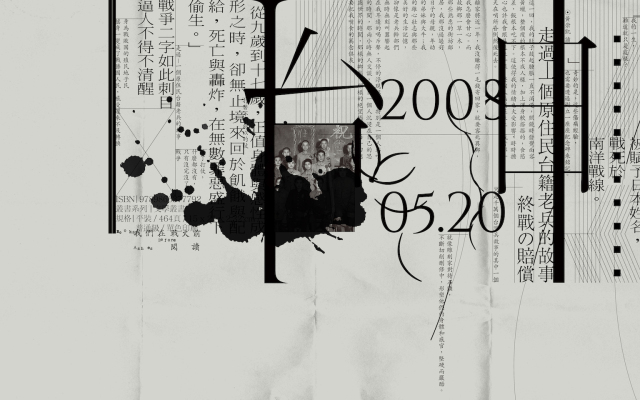【漂流計畫】關於「王榆鈞與時間樂隊」:專訪 Vocal / Guitar 王榆鈞
第一次碰到王榆鈞其實是在去年某一次排練結束之後。那時候對她還很陌生,只看到一個高個兒女孩,背著一把吉他,帶著溫暖的微笑,矗立在街旁,和眾人聊聊笑笑。後來陸陸續續聽到她開始籌備專輯,眾人都說這一切很辛苦,「可是終於,她要出自己的專輯了。」
「喜歡我音樂的人似乎都有一個老靈魂。」王榆鈞曾經這樣說過。
有些人透過詩歌認識她的音樂,有些人透過劇場作品感受到她的音樂,有些人從她的現場演出開始為她著迷,有些人則是從未錯過有她配樂的劇場作品。
滄桑的嗓音,故事的旋律,安靜的囈語,清晰的口白。王榆鈞的音樂風格獨樹一幟,很難以用現存的標籤去定義她與時間樂隊的音樂風格。
外表看起來似乎弱不經風的一位女子,其實有著無比堅毅的內在力量。她從來不去考慮事情有多難,而是專注於如何做到最好。《頹圮花園》這張專輯的誕生更是如此。因為對自己音樂風格的獨特要求,榆鈞決定自己做製作人,作品完全忠實於自己,而不被任何其他因素影響。這樣的結果是,錄音、製作的時程一再延長,常常一再重錄,只為了達到理想中的狀態。
幸運的是,經過時間沈澱、累積,最終凝聚力量產出的專輯,頗受好評。
從籌備專輯、錄音,到中山堂演出發表作品,一直到巡演結束,王榆鈞就像走完了音樂盒的紙卷一樣走了一條長長的旅程,接下來又即將前往法國,造訪影響她極深的敘利亞詩人 Adonis。
王榆鈞說她會一直做音樂到老,未來值得期待。

(漂=漂流週報,鈞=王榆鈞)
漂:《頹圮花園》收錄了許多累積了好幾年的創作,並且重新編曲。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張專輯?
鈞:
作為 singer-song writer 彈唱,同時又跟表演藝術界合作,另外還有影像的配樂,其實從聲音、音樂發展出去的任何的可能性我覺得都是有意思的。但是因為這些年來,我一直花很多時間投入跟別人的合作,好像從來都沒有好好去看過自己平常有空閒時寫的東西和做的音樂。跟別人合作時,我投入了非常多的心思,可是從來沒有用同樣投注的程度來看待我自己寫的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好像對自己很不負責任(笑)。
雖然我已經過了 30 歲了,但並不是把它當成一種精選輯的心情來做這張專輯。這張專輯的組成,應該說在生命階段的轉換這個過程裡面,我再好好的去看到自己過去的樣子,當然不能說什麼反省、檢討、調整,而是想要把某些記憶跟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東西,好好的留下來。因為人在不同的階段會一直不斷的轉變,聲音也是。之前做的專輯唱歌比例很小,大部分還是在音樂上,所以當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聲音一直在改變,就會想要把現階段的聲音記錄下來。就好像你今天聽 Cohen 或 Tom Waits 的 CD,會發現他們每一個階段的聲音都好不一樣。所以對我而言,真的就是在生命的轉換歷程裡面,想要好好的看過、想過、把他們整理好。那感覺就好像你自己將來老了之後,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當你聽到這些音樂,好像它已經擺好在你腦袋的哪一個抽屜,你知道它在哪裡,不會找不到途徑去找到它。
對我而言,這張作品是非常貼近於生活,裡面描寫的感受,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有的。差別只是,現在人好像常常在忙碌的生活裡面,不太容許自己有太多感性的部分,突然有情緒的時候,好像就會用理性去截斷那些東西,或者是你突然在這個 moment,想到一個什麼,或者跟別人擦身而過的時候,你感覺到了一個什麼氣流,那些很抽象的狀態,都只會在那個當下存在。你感受到,可是下一秒又接了手機或幹嘛,那個感覺就沒有了,可是其實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而常常在音樂裡面,我有很大的興趣去捕捉這些:我們無法言說的,在日常生活裡很多的感受。
漂:所以妳從開始創作到現在,對創作這件事情的態度,有轉變很多嗎?或是對妳來說這些轉變都記錄在這張專輯裡面了嗎?
鈞:
我覺得我對於創作的態度一直沒有變。每個人選擇創作的方式不一樣,但是對於多數創作的人來說,創作是一種跟這個世界連結、自己表達自己、和意識到自己存在的一種方式之一。基於這一點,我想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這點沒有變,有改變的是每個階段不同、體會不同,這些種種的不同造成創作想法上的詮釋不一樣,但是本質上的喜好或者是覺得創作到底是什麼,在我內心裡面那個東西是沒有變過的。
漂:那是怎麼開始跟時間樂隊合作的呢
鈞:
以前我都是自己彈唱,常常自己表演的時候就會覺得比較不有趣,想要再嘗試更有意思的,希望讓音樂有不太一樣的火花。重點是,常常我在寫這些音樂的時候,即便只有一個人彈唱,但在我的想像裡頭,它不是長這樣的,可能還有很多別的聲音。所以當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演出的時候,它是非常私密的分享,可是就音樂的詮釋上,當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好像只能完成想像裡的百分之三十、四十。基於這樣的理由,我開始跟其他人合作。但因為組樂團很不容易,所以一直不敢組樂團。那種感覺就好像你要跟別人結婚一樣,要花很多的心思、投入非常多的心力,才有辦法真的可以 do something。所以一開始只有跟 Jerry 合作,到後來我們兩個人又面臨同樣情況,覺得好像要有一個 bass 聲音比較好、好像有鼓比較好、或是很希望有一個 trumpet(小號)之類。時間樂隊的組成其實是蠻有趣的,因為這群人的聚集,並不是那種大學時代一群好朋友志同道合想做音樂,就組了一個團,日夜、吃飯、所有的生活全部都是緊密的繫在一起。我們完全是分散在各個不同的世界裡面,因為組成時間樂隊,一個一個把人拉進來,所以大家的感情跟默契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練團室裡面慢慢累積出來的,從很陌生到變成好像家人一樣,這點不太一樣。
漂:那麼多重的身分是如何影響你的創作?或是這些身分是讓你的創作更豐富嗎?或是它改變了你什麼?
鈞:
都有,它有讓我創作更豐富,也改變了我的生活,就是我沒有生活(笑),應該是說我的生活與所有事情變得密不可分、無法切割,就好像我今天答應了要做這個音樂,現在可能在跟你聊天、或看電影、或在家裡聽音樂,可是心裡就是有這件事。我有一個意識是我要做這個東西。創作是這麼深的影響我的生活,非常非常密不可分,而且是同時進行非常多的。所以常常也許會有人覺得我的思考非常的跳躍。多重身分當然有豐富我的創作,因為在每一個不同的合作裡面、每一次跟不同的人相遇,我都在認識、理解對方,因為每個人是那麼的不同,所以我也從他們身上學 習。因為每個人表達語彙不一樣,於是我要去回應的音樂語彙,也會不一樣。比如說在合作當中要求有不一樣曲風,我都當成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這些養分當我再回頭來看自己的創作的時候,是絕對有非常大的影響,我相信這些影響是好的。像我昨天看到朋友的朋友說,聽我們的音樂,第一次覺得他聽音樂好像在看故事書一樣,這是很有趣的形容,雖然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形容,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常常會這樣子形容我的作品,或者是我歌唱的表達,這些應該就是我跟表演藝術或其他領域合作所帶來的養分和影響。
漂:對你來說,完成這張專輯的意義是什麼?
鈞:
做完這個,我可以繼續前進。我感覺到自己在轉變,其實更深一層的想法是,如果我現在不把它們好好的唱、好好的錄下來,往後,我就離這些東西更遠了,會讓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唱它們,所以在我還沒有離它們太遠的時候,還有很多感覺的時候,我想把它們錄下來。錄完這張好像身上的包包變輕了,我就可以再往前走了。
漂:你期許自己未來的創作可以朝向什麼樣的方向發展?
鈞:
我期許自己創作的音樂是抽象的,並且非常真實,我希望它是純粹在探討生命中的各種面貌,以及人經歷不同階段的情感。我希望它抽象又純粹、內斂又深刻。
【漂流計畫】
由二拍子音樂發起,包含《漂流週報》的線上發行及《2015 漂流計畫音樂會》等現場演出。計畫概念來自於王榆鈞與時間樂隊此次創作《頹圮花園》專輯的核心精神,期望用質樸純粹的方式,傳達人與土地的深層聯繫以及對生命本質的思索。選擇以簡單機械原理運作的音樂盒機芯,旋律節錄自專輯裡的〈故鄉的小花〉,展開「音樂盒漂流計畫」,讓音樂盒輪流傳藝術家的手中,感受它帶給藝術家的任何想法,創作出不拘形式的作品。
【二拍子音樂】
以「二拍子」為名,取自音樂用語,而心跳的頻率也是二拍子。彷若是一直一直跳動著,不斷地向前走去,跳動著、跳動著,極具生命力。